
文中有数据派THU福利哦

为什么科学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出现?因为铁律看起来是一个糟糕的想法。
“认可……理论的唯一前提是它们的内容与观察到的事实相一致。” 这听起来和艾萨克·牛顿或者理查德·费曼说的话一样符合科学精神,然而这句话是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写的。亚里士多德是一位有条理的观察者、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也是一流的知识分子。他把理论解释现象的能力放在了首位。
那是什么阻止了他在近现代科学革命发生的2000 年前创造近现代科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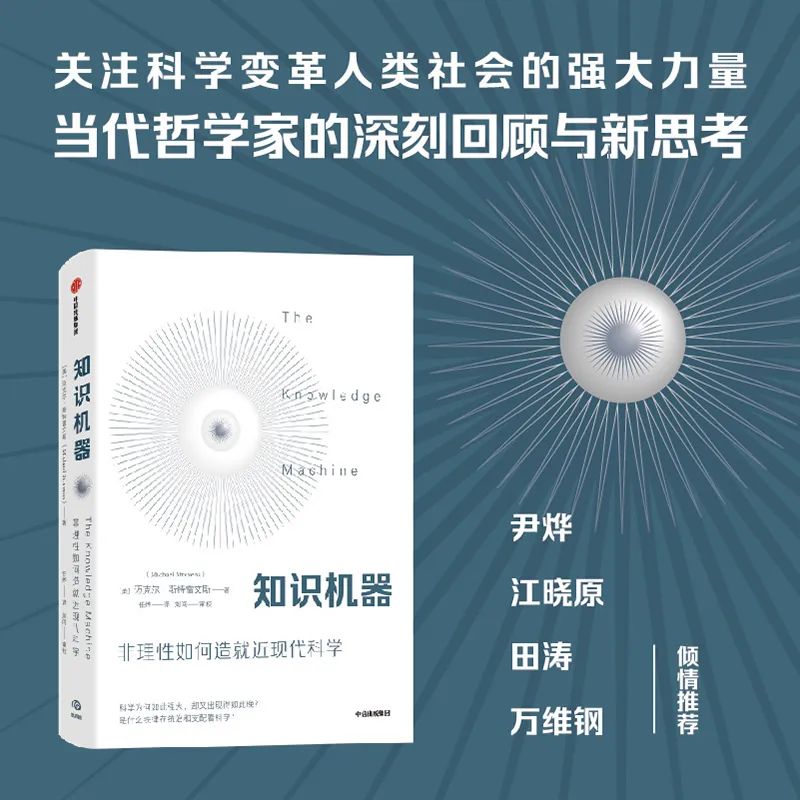
通过写一部科学革命史来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很诱人的提议,我们会看到在17 世纪起作用的那些社会、知识和经济因素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几乎或者完全不存在:笛卡儿和玻意耳提出的机械论的影响,数学在物理理论化进程中的应用,印刷、透镜磨光及玻璃吹制等新技术,以及人们开始把对自然界的探索看作是一种高尚的宗教崇拜。
这会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然而,这种叙述分辨不出哪些因素对近现代科学本身至关重要,哪些因素只是对以17 世纪的那种方式发展的近现代科学至关重要。当然,没有数学就不可能有伽利略或牛顿,但并非所有的科学研究都需要高等数学(化学的发展就不需要)。虽然没有原子论就不可能有玻意耳或惠更斯,但并非所有的科学都是关于分子间相互作用的(自然选择进化论就不是)。尽管伽利略和其他人用望远镜撼动了17 世纪的天文学,但第谷·布拉赫凭借肉眼获得的行星观测结果就足以支撑新的引力理论。
因此,为了搞清楚科学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出现,我没有从叙述历史开始,而是从哲学角度把近现代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找出它的必要条件:在解释其做出新发现的能力时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结果我发现,这个必要条件就是解释的铁律。亚里士多德和其他许多自然哲学家,之所以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时代都没能启动我们成为“近现代科学”的知识机器,就是因为他们虽然重视观察,但没有创造出铁律。
我们可以把亚里士多德和牛顿做个对比。他们俩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想找到一种解释物体运动和变化方式的宏大理论。然而,他们的方法却大相径庭。亚里士多德对自己的假说进行了严格的哲学检验。而牛顿则对自己的假说进行了严格的定量检验,要求它们不仅能解释运动的特性(圆周运动与直线运动、上升与下降),还要解释最精密的细节,例如开普勒定律所描述的行星的精确轨迹。

事实证明,定量检验更为重要。尽管亚里士多德仔细研究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而且非常关心自己的假说解释这些现象的能力,但他通常满足于解释普遍的模式,而不是具体的细节问题。然而,科学发现真相的能力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这些微小的事实。
库恩也看到,人类要对这些极其重要的微小事实保持长久的关注是极其困难的。这些细枝末节很少包含真正有趣的内容,把它们从自然界中提炼出来往往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工作;而高贵的脑力活动(不管是概念性的、哲学性的还是系统化的)总是在引诱着经验主义研究者离开实验台或者观测站,走向思想的闪光之地。大多数科学工作更像是簿记或者做长除法,而非富有诗意的自我表达或者极地探险。伟人几乎不可能去追求这样的生活。
铁律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并不是试图美化明显很枯燥的东西,而是采用了一种更间接、更迂回的策略。我之前已经解释过,铁律把科学争论设定成一个捍卫和攻击假说的棋局。在这个棋局中,只有一种走法是合法的,那就是经验性检验。攻击一种假设是因为它没能解释某些观察到的事实,而捍卫这种假设,就要证明失败仅仅是表象,是由设备故障、不利条件或者错误的假设导致的。流畅的言辞、高度抽象的研究、说教,还有其他任何形式的花言巧语或者宏大思想都不能带来胜利。要想赢得比赛, 玩家们必须完成细致入微的观察。

亚里士多德如果要遵从铁律的话,就得根据这个游戏的规则来进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像所有的狂热玩家一样,他不得不放弃追求更高的和谐性。由此被解放的体力和智力将朝着仅存的一个方向流动,流向冷酷无情的经验性检验。如果这样,那么到公元前322 年他去世的时候,一场经典的近现代科学革命很可能已经全面开始了。
但亚里士多德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就算他想到了这样一个游戏,他也会马上否定这个想法。他不打算放弃哲学推理。
他不是空想家—他并不提倡与观察结果相悖的哲学推理。事实上,他主张把哲学与观察结合起来,而且当观察结果与哲学观点发生冲突时,亚里士多德更看重观察结果。在批评某些前辈时,他写道:他们对现象的解释与现象本身并不一致。原因是他们所假设的基本原理是错误的:他们有某些预先确定的观点,并决心要让一切都与之相符……似乎有些原理并不需要根据它们的结果来判断,尤其不需要根据最终结果来判断!而那个结果……在自然知识中……就是感知到的现象。
因此,铁律不会给亚里士多德带来任何新的信息来源或者任何新的处理信息的方法,而只会让他抛弃哲学。这看起来是一场不公平交易:放弃一个有价值的信息来源,也就是哲学推理,却没有任何回报。这显得很不合理,而且野蛮,可以说是完全不可理喻。

同样,铁律也会有意忽略认可某种看法的宗教、精神和神学理由。纵观历史,信徒们始终认为自己的宗教教义会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当然还有生物领域产生影响。1841 年至1866 年间, 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担任院长的威廉·休厄尔思想上遭受的痛苦,戏剧化地体现了这种认知与铁律的潜在冲突。通过研究新发现的化石记录,休厄尔看到了大规模物种形成的事件,他认为只有上帝的介入才能解释这种现象。因此,全面了解生命史需要对地质学、生物学和神学进行统一的研究。但休厄尔从大学时代就印在脑海中的铁律却禁止他在科学著作中进行这样的综合研究。尽管这看起来是错的,甚至有点儿荒谬,但他还是克服了自己的疑虑,向科学方法低头了。
我们可以把休厄尔困惑的根源投射到近现代科学出现之前数千年的历史中。在整个欧洲中世纪和大致同期的伊斯兰文化黄金时代,你会发现思想家是通过天文学、光学、医学等方法来探索自然界的运转方式的。这些思想家中没有一位想到过铁律之类的东西,他们也不可能想到。他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笃信着神。他们很清楚,对神或“神的计划”的认识,可能会告诉我们物质世界(历史、生命体、行星系统等)中事物布局的方式。尽管神学为经验性研究提供的帮助可能相对比较少,但这种可能性还是值得探索的。
然而,铁律却坚决禁止这种探索。在科学领域,只有经验性推理才算数。因此,对于那些和休厄尔不同,没有见识过铁律指导一系列惊人发现的人来说,科学研究似乎是一种受到故意阻碍的探索世界的方式。草率地禁止神学思维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毫无意义,就像草率地禁止哲学思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毫无意义一样。因此,在奥古斯丁、阿维森纳、阿维洛伊和阿奎那生活的那几个世纪里,没有出现过类似铁律的东西也就不足为奇了。
即使是像勒内·笛卡儿这样处在近现代科学革命风口浪尖的早期的现代思想家,也不能忍受铁律将经验性研究与神学研究分割开来的做法。笛卡儿的自然哲学思想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了上帝的力量与监督作用:例如,他认为是上帝确保我们的头脑中储存着非常适合思考这个世界的概念,是上帝让构成世界的物质处于匀速圆周运动的状态。在笛卡儿看来,在研究自然界时,像铁律那样禁止考虑上帝的存在与属性(全知、全能、仁爱)这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是相当难以理解的。因此,我们会发现,笛卡儿的文章和在他之前几乎所有人的文章一样,对于铁律绝对性的要求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在17 世纪40 年代,尽管培根和其他一些激进分子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科学仍然不愿现身。

这就是科学在人类历史中出现得如此之晚的原因:它似乎是一项不大可能成功的事业,一种有意营造知识匮乏的活动。铁律强调观察很重要,这一点没什么难接受的,但它最难接受的一点是坚持认为只有观察才是重要的,这条“反智”的禁令关闭了头部除眼睛之外的所有部位。
于是,一个恶性循环让人类思维无法获得感受科学的能力:如果不去在实践中检验铁律,是无法理解它有多大用处的,但如果不先大致了解一下它有多大的用处,就没有理由去检验它。事实上,不检验它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它忽视了被认为不可或缺的知识来源。这个循环的逻辑困住了古希腊人,也困住了中世纪和早期的现代哲学家,比如笛卡儿。我猜想它同样也困住了中国和朝鲜、印度和波斯、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的思想家。就算他们考虑过铁律,他们也会对它嗤之以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从未有过如此荒谬的想法。
1859 年,在休厄尔试图用复杂的神创论思想解释化石记录的20 年后,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自然选择进化论给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震惊了整个社会。在创世的问题上,上帝似乎要被排除在外了。
1878 年,进化论学者乔治·罗曼尼斯(George Romanes)痛苦地写道:“无信仰的闸门已经打开,无神论正在向我们涌来。”这绝不是达尔文一个人造成的。地质学家已经对“大洪水”的存在产生了怀疑;考据学者证明《圣经》是由不同时代的很多不同的作者所写的文章汇编而成的;法国的革命者、英国的诗人和德国的社会思想家正在想象一个不被宗教组织束缚的世界。随着19 世纪欧洲的发展,信仰的披风开始从人类精神的肩膀上滑落。
今天,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科学家信仰上帝。即使是这些信徒,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认为自己的精神信仰能够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影响到他们的研究。出于各种实用目的,他们赞同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观点,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对两个完全不同的主题进行研究的合法形式,它们是“不重叠的领域”。如果你想理解生命的意义,你一定要学习宗教。然而, 要了解行星的运动和物种的起源,你只需要进行经验观察。所以对当代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铁律把宗教因素排除在科学争论之外没有丝毫不合理的地方。

铁律将哲学论证排除在外的做法也是一样。例如,大多数物理学家都认为,试图解释量子力学,使人类能够理解它,就是在浪费时间。只要利用其数学机制做出预测并构建浅层解释就可以了,他们会说:“闭上嘴,动笔去算。”物理学家史蒂文·温伯格更进一步说:据我所知,在战后积极参与物理学研究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的研究得到过哲学家工作成果的极大帮助。
如今,人们已普遍认为宗教与哲学因素对科学无关紧要,这是否意味着铁律已经失去了逻辑上反常的表象呢?它是不是不用再删减看似合理的非观察性的理由了呢?那样的话,我们就拥有了值得称赞的科学,它不仅有丰硕的成果,还是理性的典范。
然而我们并未拥有这样的科学:即使在今天,铁律也给人一种不理性的感觉。不过,这里的例子不再是少数认为他们信仰的神明显在物质世界中发挥作用,或是试图通过哲学方法来获得理论认识的科学家。我想到的是很多当代科学家,包括温伯格本人,都广为称颂,认为能够解释自然界奥秘的一种推理形式:以一种理论的美为理由来论证其真实性。
铁律禁止科学家在正式的沟通渠道中使用所有这样的论据。因此,现代的研究者如果认为审美素养能为我们指明通向真理的道路,就必定觉得科学方法故意忽略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说,尽管科学方法很有成效,但严格地说,它违反了理性原则。
——节选自中信出版社·鹦鹉螺工作室《知识机器:非理性如何造就近现代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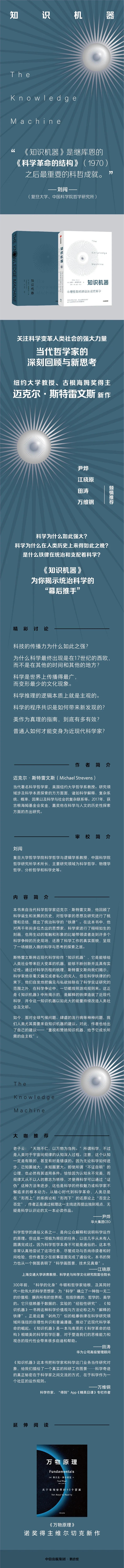


点点为数据派THU的粉丝们争取了3本赠书福利!欢迎小伙伴儿在下方留言区畅谈对“非理性如何造就近现代科学”的看法,我们将为点赞数最高(截止到2022年8月2日早8点)的3位读者免费送上此书~小编会联系你们哦!(之前获得过赠书的粉丝不能参与)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