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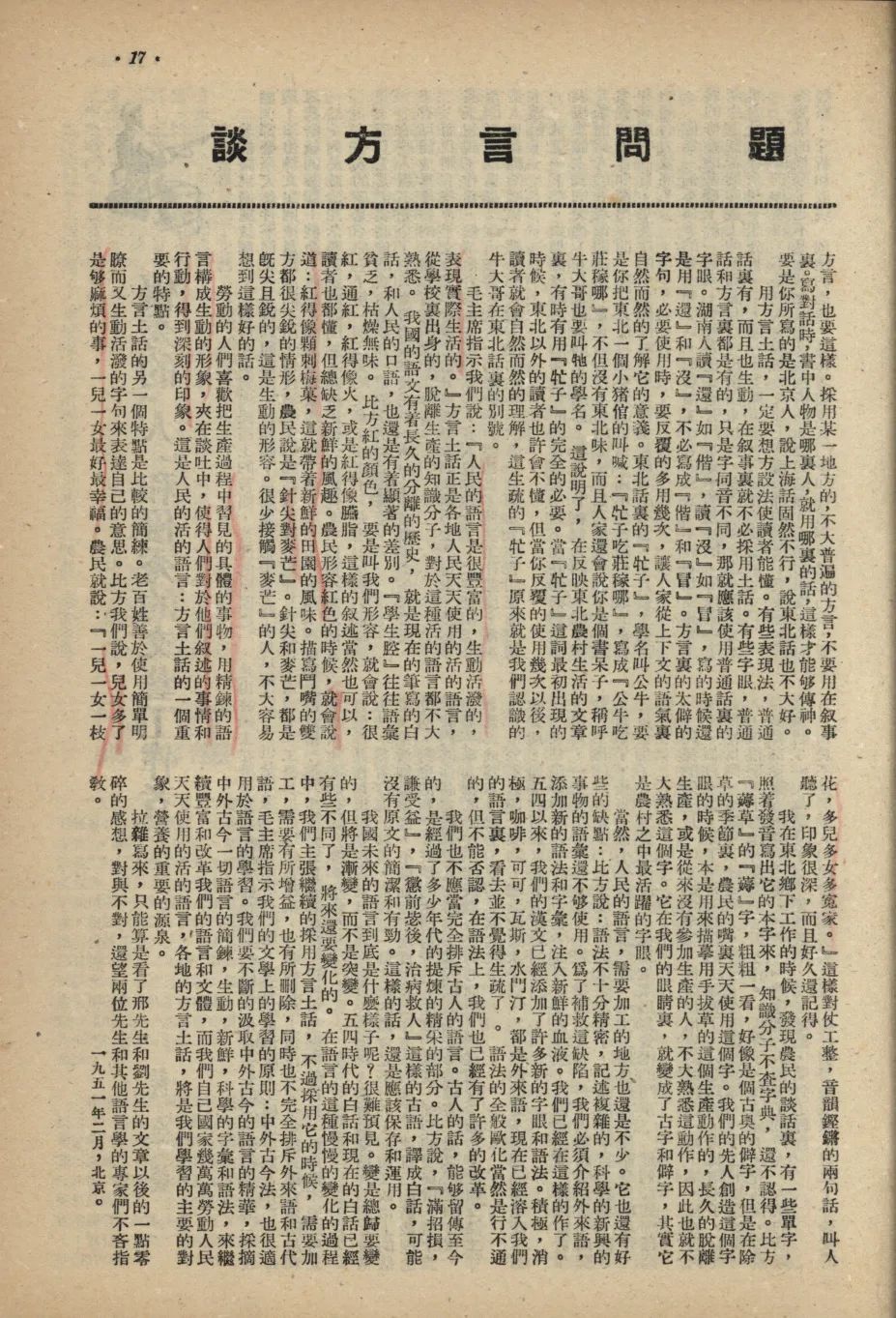
看了邢公畹和刘作骢两先生的文章,我也想来凑凑热闹,谈谈我对这问题的看法。
两位先生涉及的问题是很多的,本文不能一一谈论,我只根据创作实践的经验,说些点点滴滴的感想。
就我所知,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正式提出“方言文学”的口号,也没有人把这口号“作为对反动统治阶级斗争的策略之一”而提出。自然,文学是对敌斗争的武器之一,但不是光指文字,主要指内容。文字,方言,是“我能往,寇亦能往”,敌我双方都能利用的。同样的方块字,蒋介石匪帮用来诌反动的胡说,我们用来写革命的文章,区别主要在内容,而不在文字。五四时代,中国文字有过一次显著的改革,那时候,用文言的多半是些守旧的,甚至反动的人物,用白话的是进步的,革命的势力。但是不久,反动的统治阶级,特别是蒋介石匪帮也用白话了,蒋匪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都是用白话来创作的,但是他们这样做,决不能,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反动的面貌和本质。这也说明了文学的革命与否的基本的标志,不是文字,而是内容。
邢先生说:过去我们写农民,用方言,都有革命的意义。现在全国解放而且统一了,“特别是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的今天”,似乎不能再用方言来创作,来写农民了。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又说:“方言文学”这个口号“不是引导着我们向前看,而是引导着我们向后看的东西;不是引导着我们走向统一,而是引导着我们走向分裂的东西。”
前面说过,没有人提出“方言文学”的口号,但我们过去曾用方言来创作,来写农民,将来也会用方言创作,也还是要写农民的。至于用方言是否会引导若我们“向后看”,并且“走向分裂”呢?我以为不会。斯大林说的对:“方言习惯语和同行语是全民语言的支脉,并且服从于全民语言。”采用方言,不但不会和“民族的统一的语言”相冲突,而且可以使它语汇丰富,语法改进,使它史适宜于表现人民的实际的生活。
邢先生又问:“在今天,我们是应该以正在发展中的统一的民族语来创作呢?(那就是说在我们的创作中要适当地避开地方性土话。)还是应该川方言来创作呢?(那就是说在我们的创作中特别去使用并且强调那些地方性的土话)”
我以为我们在创作中应该继续的大量地采用各地的方言,继续的大量的使用地方性的土话。要是不采用在人民的口头上天天反复使用的生动活泼的,适宜于表现实际生活的地方性的土话,我们的创作就不会精彩,而统一的民族语也将不过是空谈,更不会有什么“发展”。
在创作中怎样采用方言的问题,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我们的文字是统一的。写在纸上的汉文是全国一致的方块字。而我们口说的方言却非常之多,非常之复杂。特别是南方,不但省和省之间的口音有重大的区别,有些交通不便的地区,县和县之间的口音,也各不相同。但是,正如邢先生所说,北方话,特别是北京的方言,已有作为中国汉族标准语的趋势。北方各省的话,大致都相同,懂得的人多,光有音,写不出字来的词,比较的少。而南方话,特别是广东,福建和江浙等地的部分的土话,在全国范围里不大普遍。这几个地方的有些方言,写在纸上,叫外乡人看了,简直好像外国话。这样的方言,不宜全部的采用。鲁迅和茅盾先生的创作,并不全部使用他们的家乡话,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就是难懂的南方话,我们也应当汲取它的丰富的字汇,精妙的语句,来改进我们的语言。“像煞有介事”已经成了普通话。最初使用这话的时候,除了江浙一带以外,懂得的人是很少的吧,但是现在,凡是能看书报的,都懂它的意义了。北方土话普遍性很大。全国除了交通不便的地区,大都能懂“红楼梦”里的语言,其实这就是北京的方言。
在创作上,使用任何地方的方言土话,我们都得有所删除,有所增益,换句话说:都得要经过洗练。就是对待比较完美的北京的方言,也要这样。采用某一地方的,不大普遍的方言,不要用在叙事里。写对话时,书中人物是哪里人,就用哪里的话,这样才能够传神。要是你所写的是北京人,说上海话固然不行,说东北话也不大好。
用方言土话,一定要想方设法使读者能懂。有些表现法,普通话里有,而且也生动,在叙事里就不必采用土话。有些字眼,普通话和方言里都是有的,只是字伺音不同,那就应该使用普通话里的字眼。湖南人读“还”如“偕”,读“没”如“冒”,写的时候还是用“还”和“没”,不必写成“偕”和“冒”。方言里得太僻的字句,必要使用时,要反复地多用几次,让人家从上下文的语气里自然而然的了解它的意义。东北话里的“牤子”,学名叫公牛,要是你把东北一个小猪倌的叫喊:“牤子吃庄稼哪”,写成“公牛吃庄稼哪”,不但没有东北味,而且人家还会说你是个书呆子,称呼牛大哥也要叫它的学名。这说明了,在反映东北农村生活的文章里,有时有用“牤子”的完全的必要。当“牤子”这词最初出现的时候,东北以外的读者也许会不懂,但当你反复的使用几次以后,读者就会自然而然的理解,这生疏的“牤子”原来就是我们认识的牛大哥在东北话里的别号。
毛主席指示我们说:“人民的语言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方言土话正是各地人民天天使用的活的语言,从学校里出身的,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对于这种活的语言都不大熟悉。我国的语文有着长久的分离的历史,就是现在的笔写的白话,和人民的口语,也还是有若显著的差别。“学生腔”往往语汇贫乏,枯燥无味。比方红的颜色,要是叫我们形容,就会说:很红,通红,红得像火,或是红得像胭脂,这样的叙述当然也可以,读者也都懂,但总缺乏新鲜的风趣。农民形容红色的时候,就会说道:红得像颗刺梅果,这就带着新鲜的田园的风味。描写斗嘴的双方都很尖锐的情形,农民说是“针尖对麦芒”。针尖和麦芒,都是既尖且锐的,这是生动的形容。很少接触“麦芒”的人,不大容易想到这样好的话。
劳动的人们喜欢把生产过程中习见的具体的事物,用精练的语言构成生动的形象,夹在谈吐中,使得人们对于他们叙述的事情和行动,得到深刻的印象。这是人民的活的语言:方言土话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方言土话的另一个特点是比较的简练。老百姓善于使用简单明了而又生动活泼的字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比方我们说,儿女多了是够麻烦的事,一儿一女最好最幸福。农民就说:“一儿一女一枝花,多儿多女多冤家。”这样对仗工整,音韵铿锵的两句话,叫人听了,印象很深,而且好久还记得。
我在东北乡下工作的时候,发现农民的谈话里,有一些单字,照着发音写出它的本字来,知识分子不查字典,还不认得。比方“薅草”的“薅”字,粗粗一看,好像是个古奥的僻字,但是在除草的季节里,农民的嘴里天天使用这个字。我们的先人创造这个字眼的时候,本是用来描摹用手拔草的这个生产动作的,长久的脱离生产,或是从来没有参加生产的人,不大熟悉这动作,因此也就不大熟悉这个字。它在我们的眼睛里,就变成了古字和僻字,其实它是农村之中最活跃的字眼。
当然,人民的语言,需要加工的地方也还是不少。它也还有好些的缺点:比方说:语法不十分精密,记述复杂的,科学的新兴的事物的语汇还不够使用。为了补救这缺陷,我们必须介绍外来语,添加新的语法和字汇,注入新鲜的血液。我们已经在这样的作了。五四以来,我们的汉文已经添加了许多新的字眼和语法。积极,消极,咖啡,可可,瓦斯,水门汀,都是外来语,现在已经溶入我们的语言里,看去并不觉得生疏了。语法的全般欧化当然是行不通的,但不能否认,在语法上,我们也已经有了许多的改革。
我们也不应当完全排斥古人的语言。古人的话,能够留传至今的,是经过了多少年代的提炼的精彩的部分。比方说,“满招损,谦受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样的古语,译成白话,可能没有原文的简洁和有劲。这样的话,还是应该保存和运用。
我国未来的语言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很难预见。变是总归要变得,但将是渐变,而不是突变。五四时代的白话和现在的白话已经有些不同了,将来还要变化的。在语言的这种慢慢地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主张继续的采用方言土话,不过采用它的时候,需要加工,需要有所增益,也有所删除,同时也不完全排斥外来语和古代语,毛主席指示我们的文学上的学习的原则:中外古今法,也很适用于语言的学习。我们要不断地汲取中外古今的语言的精华,采摘中外古今一切语言的简练,生动,新鲜,科学的字汇和语法,来继续丰富和改革我们的语言和文体,而我们自己国家几万万劳动人民天天使用的活的语言,各地的方言土话,将是我们学习的主要的对象,营养的重要的源泉。
拉杂写来,只能算是看了邢先生和刘先生的文章以后的一点零碎的感想,对与不对,还望两位先生和其他语言学的专家们不吝指教。一九五一年二月,北京。
(原载《文艺报》1950年第10期)
微信编辑:吕漪萌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