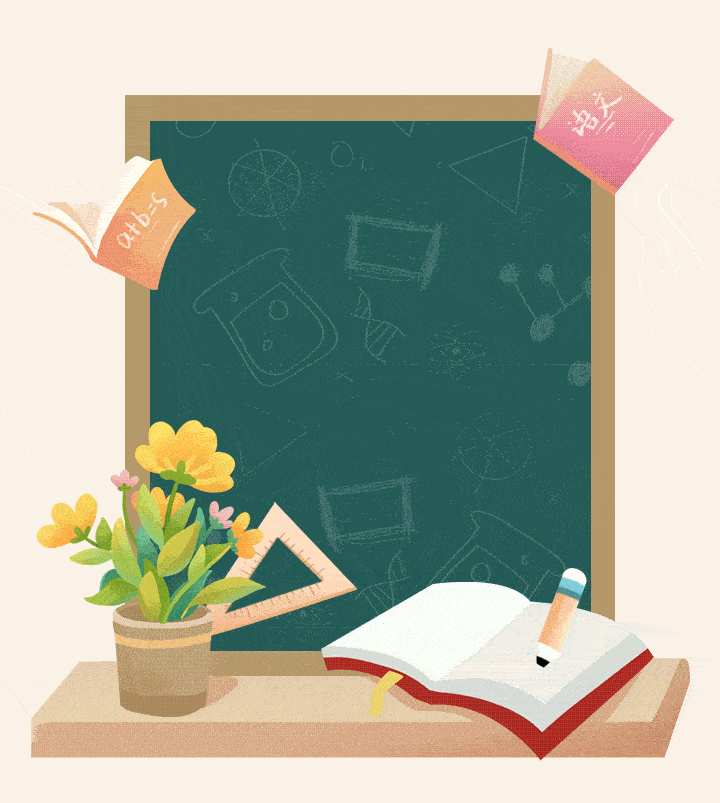
酉老师
曾旭临
我读小学时,有个老师,姓酉。酉老师的长相,整体来看,清秀,但眉宇间,彻彻底底英气!酉老师当过兵,转业回来做了民办教师,不久又做了我们大队小学的校长。他教了我一年,五年级的数学。
许是毕业班的缘故吧,酉老师给我们安排的教室,“规格”是最高的。那教室,虽然跟低年级一样的泥筑瓦盖,却是现成的石桌石凳,不必自己从家里搬来桌凳上课。夏天,凉快;冬天,编个草墩儿垫屁股底下,不得冷。教室里的我们,有种优越感;教室外的他们,羡慕并渴望着:“明年该我们了”“后年该我们了”……
就这间教室,我被酉老师吓过一回。那天,酉老师拿着根木头尺子在讲课,讲得脖子上的青筋跟胖蛐蟮儿一样。坐在讲桌前面第二排的我当时就走了神,侧过头跟同桌说:“你看酉老师的颈……”我“子”字都还没有说出来,就听见“唰唰”声响,那根原本拿在酉老师手上的木头尺子,赫然横在我和同桌之间的石头桌子上。我立马端坐,酉老师啥也没说接着讲课。
说实话,当时我确实是被吓了一跳,但是,这被吓的感觉没几天就消散了。久久不能消散的,是几天之后心里升起的疑惑——那木头尺子,要从酉老师手上串到我们的石头桌子上,必须空中、讲桌前第一排石桌、再空中,出手高了低了都不得行;那木头尺子,刚好横在我和同桌之间,出手轻了重了或者左了右了,也不得行:酉老师是怎么做到的呢?疑惑归疑惑,反正我后来再也没打过“梦觉”。
那会儿的学校,是有土地的;每周两节劳动课,老师带着学生干农活。我们大队小学在围墙外有一亩多地,每个班分管两分儿地。
同学们对劳动课的热爱,远胜于对体育课的热爱。体育课,老师集合整队,给一个篮球,然后解散。男生,坑坑洼洼的泥土坝子上追着抢,许多人到下课都没有摸着篮球一下;女生很知趣,不去抢篮球,围墙边边跳绳,但小眼睛全盯在篮球上,随时提防被冲撞。劳动课就不一样了。学生个个手里有事干:拿锄头的挖窝窝儿,拿盆盆儿的下种子,拿粪瓢的候在厕所里水沟边,拿扁担粪桶的抬着粪和水风风火火的串;酉老师,跟带兵打仗一样,随时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锄头要这样拿手上”“不要掉茅厕里去了哈”……
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年大丰收:麦子、油菜籽装满了许多大口袋,放在老师办公室旁边的空教室里;麦草杆儿、油菜杆儿被捆成捆,靠学校围墙放着,里里外外排得满满的。
当麦子换成挂面、油菜籽榨成清油后,全校的“野营拉练”就开始了。
酉老师自任营长,穿了洗得泛白的绿军装,扎一根陈旧的军用皮带,带两个“小兵”:一个司号员,手握从卡车上拆下来的废旧喇叭;一个通讯员,肩挎贴着纸裁红五星的空书包。然后,一个班集体为一个连,老师做连指导员,班长做连长。没有排级编制,连级下面直接就是班。我是全校学生的“大队长”——相当于后来的“学生会主席”——照理,该做个副营长。结果,别说副营长,我连个连长都不是,当了个小小的班长!我不知酉老师是怎么想的,心里很不舒服。
不过,这不舒服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野营拉练”实在是太有趣了。
军号一响,全营集结。营长双手叉腰站在高台上,左右两边是司号员和通讯员,下面是穿得杂七杂八、手握红缨枪的战士们。“同志们——”营长的右手从腰间离开,往上,在肩高处圈一个圈儿,再猛力一举,然后收回继续叉腰,“据我方侦查人员报告,敌人盘踞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头上。我们现在去消灭它,有没有信心?”战士们斗志昂扬:“有——”
部队出发了。大家背着学校分发的挂面、清油,以及井水、柴火与锅瓢碗盏,长蛇状游走在山野之间。开始,队伍整整齐齐,后来,经不住军号声里几次紧急卧倒:有的柴火捆散了,有的锅儿“叮咚”掉路上了,还有的,丢了红缨枪枪头,拿着根挂了几缕红须须的竹子棒棒往前疾走……
终于,有敌人盘踞的山头出现在眼前。营长下令:“各连分头行动,进入预定位置待命。”通讯员立即跑步各连传达。不久,队伍就沿山脚把整个山头包围了。接着,又一道命令传来:“全体卧倒!注意隐蔽!”军令如山,战士们顾不了许多,立即就地趴下。我左边那位,压着一堆狗屎,居然一动不动。我右边那位,压着一窝蚂蚁,鼓着个腮帮子把接连不断爬上手臂的小不点儿吹得到处飞。我一边腾出手板儿鼻前扇风驱赶恶臭,一边“嘿嘿嘿”的笑着看右边那位跟蚂蚁较劲儿。有两个宪兵走来了,我赶紧忍住,伏在地上一动不动。宪兵在我身后磨蹭了一会儿,走了。
不知过了多久,营长身边的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大家迅速起身,跟斗扑爬地往上冲。“冲啊——”“冲啊——”的呐喊声,满山坡都是,吓得草丛树梢的鸟雀惊慌失措遍天飞。我们连是最先冲上去的,还抓获了几个敌人。在给几个俘虏背上张贴写有“俘虏”字样的纸片时,大家却望着我笑,笑得我莫名其妙。有人实在忍不住了,说:“你……哈哈……你……哈哈哈……你背上贴着‘逃兵’呢!”我立马回过神来:“狗日的宪兵!”骂完,我照样兴高采烈,跟大伙儿一起,埋锅烧水大碗吃面,任随背上那张写了“逃兵”字样的纸片迎风招展。
“野营拉练”后,老师办公室旁的空教室又空了。但是,学校围墙的里里外外,依然靠着成排的麦草杆儿、油菜杆儿。
酉老师为了我们班有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上,就让我们中午在学校煮饭吃,然后上午自习。于是,我们几个同学一个组,围墙边垒灶头炒菜煮饭。柴火,就是靠着围墙的麦草杆儿、油菜杆儿。
有一天午自习,酉老师突然从讲台飞跃出门,惊得同学们全体起立向外张望。只见酉老师几个起落,然后就地一滚,当即就灭了围墙边一团熊熊烟火。酉老师站起来拍打草绿色背心上火星的时候,那件被他在飞跃中扯下来抛向空中的衬衣刚好飘落到地上。同学们赶紧跑出教室,有的去搀扶酉老师,有的满坝子去找被崩飞了的衬衣扣子。回到教室后,有几个女生把头埋得很低,等着挨批评,可酉老师只说了三个字:“做作业!”
后来,有同学觉得,对于这件事,酉老师应该说点啥才对。但是,我却认为:酉老师已经用自己的行为教导了同学们许多许多,哪里还用得着再费口舌!
升学考试后不久,学校大门边的土墙上贴出一张喜报,上面是被录取学生的名字和分数。围观的人群中,有我和我的同学们,还有酉老师。我考了个不前不后中间走的分数,心里很不是滋味儿。酉老师反复念着我的名字和分数,不停地摇头,满是失望的样子,我更加无地自容!
9月1号那天,我从初中校报名回来,绕道去了大队小学。酉老师正在忙碌,身边围着一大群小学生。我不忍打扰老师,就远远地站着望,望得自己热泪盈眶。
终于,酉老师走来了。他在笑,笑得很亲切;他在喊,喊着我的小名儿。我的眼泪“唰”就下来了。
“老师,我今天去初中校报名才知道:我的升学总分少加了20多分,我其实是我们小学第一名。”我说。
“这就对了!……我说嘛……这就对了!”酉老师因忙碌而略显疲惫的脸上,顿时容光焕发。
“谢谢您,老师!”我一面说着,一面弯下腰,给酉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走的时候,酉老师把我送到校门口。我走得很远了,还能听见酉老师在反复叮嘱:“林娃——攒劲读书——攒劲读书——”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曾旭临(成都东部新区石板凳学校语文教师)
配图:方志四川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