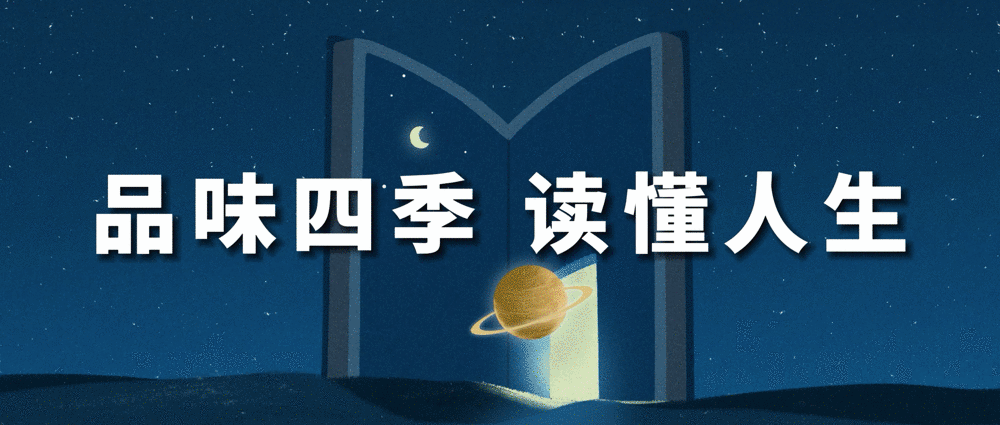

尽管父母早已搬到故乡邻近的镇上居住多年,但我对那个自己生长了18年的老家,总是心心念念。郭大姐在微信里一次次邀请,她总是用“回家看看”这样的字眼,让我无法拒绝。
去年国庆假期,因了郭大姐的邀约,我说走就走。
一个半小时,不到百公里的路程,我回到了魂牵梦萦的老家——大连市普兰店区墨盘街道,在普兰店撤市改区之前称为墨盘乡。
是的,我没有写错,是墨盘,而不是磨盘。
郭大姐说,磨盘更像一个器物,石材,冰冷而缄默;而墨盘是温润的,有质感的,是有文化的,是可以开口说话的。
至今,墨盘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倒是墨盘的花生近几年越来越有声名。
许是山东人后裔的缘故,墨盘人对种花生很有心得。我本人祖籍山东莱阳,我没有考证莱阳是不是花生之乡,祖上第一代闯关东的人或许带着花生种子扎根墨盘也未可知,反正我是吃着花生长大的墨盘人。
我对土壤没有研究,但有专家说墨盘乡的土壤最为适合花生的生长。那种土,不像黑土地的黑土那么黏稠,也不像沙地那般疏松。在墨盘,人们称花生叫“果子”或“地果”,它是墨盘人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食物。
童年,尽管我不是生产队的劳动力,但对于花生的播种和收获,我倒是略知一二。
种果子之前,是需要将花生种用水泡过,但不要泡到发芽。那感觉就是现在饭店里“花生拌萝卜皮”那道凉菜中花生的火候,很可口的。
大面积地收获花生,需要用犁铧从花生的根部更深处将田垄挑开,乡亲们连秸带根轻轻拍打,把浮土抖落干净,全部拉到生产队场院上晾晒。
这时花生地里必然会有少量花生散落在泥土里,屯子里的男女老少早已等在地边,等生产队长一声令下,大家蜂拥而入,挥起耙子翻动泥土,把残存的花生捡拾进自己的筐里。这种翻捡花生残留果实的行为,老家人称之为“拦果子”或“拦地果”。生产队的花生是要交公粮的,这捡来的“果子”才是自己的,炸花生米吃也好,晒干了生吃也好,榨油吃更好。
大队上或者公社多半都有油坊,把花生去皮后送到油坊,花几块钱榨出喷香的豆油,压出来的花生饼也异常好吃。花生饼是我童年的零食,兜里揣上一块,饿了就咬一口,解饿解馋。
墨盘的孩子都是吃着果子长大的,他们健康而聪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墨盘的花生就是这一方水土的珍宝。

我18岁随在电业部门工作的父亲离开老家,搬到了附近的小镇城子坦。不管搬到哪里,我唯独吃花生的习惯一直没变。我最爱吃刚从土里拔出来的花生,新鲜的,湿漉漉的,一咬就嚼出白白的汤汁……我只吃名叫“大白沙”“小白沙”的品种,现在好像叫“海花”,这是郭大姐家姐夫告诉我的。
姐夫退休前是乡里的农业助理,标准的国家公务员。按说,退休了他就该到县城里去养老,那里的房子都装修好了,闲置好几年了。
但姐夫是个倔脾气,认准的理儿,谁也改变不了他。郭大姐做过副乡长、副书记、乡人大主任,官儿比姐夫大多了,但在家里就是拗不过姐夫。
姐夫在街道文化站边上,租了一个足有五六个篮球场大小的库房,成立了一个专门收购当地花生的合作社。每年秋天,姐夫将收购来的优质花生集中卖给山东的花生出口企业,按需求分别出口到欧盟和日本。
这样,墨盘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就彻底没了,只管每年好好种植花生,秋收后随行就市,一并卖到姐夫的合作社,然后安心过冬,享受脱贫致富以后的悠闲生活。
姐夫告诉我,他每年收购花生需要很多现金,这是个巨大的压力。每年都东拼西凑,求东家,借西家,熬了一年又一年。眼看着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自己也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墨盘街道靠花生致富的消息不胫而走,临近街道种花生的农民也开始将花生卖到墨盘,姐夫的合作社无法消化这么多花生。姐夫跟街道领导合计,通过招商引资,又引进了好几个花生收购和加工企业,这样,出口连带内销,墨盘的花生产业越做越大,成了大连市的花生集散地。
天有不测风云。去年,在大连市内打拼的儿子,不幸因病离世,才三十来岁,还没有成家。郭大姐和姐夫一家的天塌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夫妻俩万念俱灰,什么也不想做了。但秋天来临,看着白花花的花生,看着乡亲们期待的眼神,姐夫含着眼泪打开了仓库的大门……

我说,姐夫我写写你吧?
姐夫说,写可以,但不要提他的名字,或者干脆就把“花生”作为他的名字。
一段时间以来,我特别想找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盖一处房子,把我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书都放进去,盘上东北火炕,再留出喝茶、写字的空间。特别是要有一个院子,种些时令蔬菜,栽些瓜果梨桃,最要紧的,是一定要种些“大白沙”“小白沙”花生。有时闭门谢客,读书思考;有时高朋满座,曲水流畅……
这一趟故乡之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文:李皓,本文有删减
来源:《品读》2022年第9期
责编:张初
校对:郭艳慧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