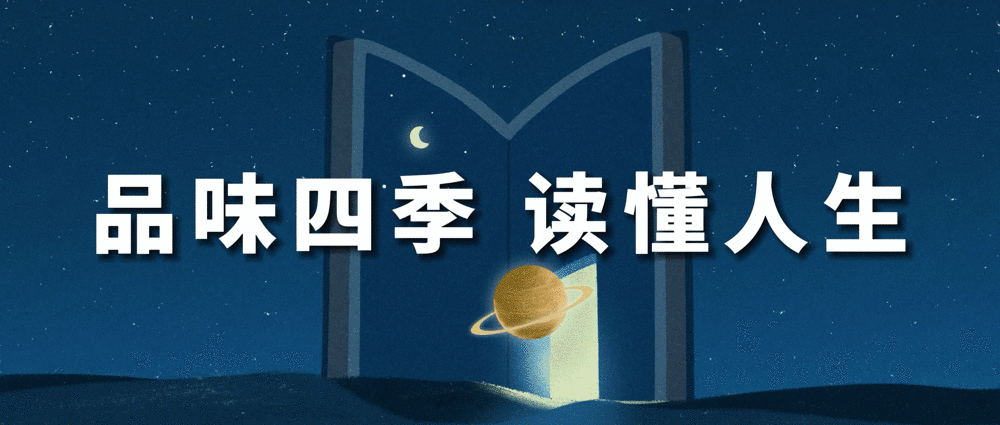

*本文为《品读》2022年第11期内容
我在乡村中学当老师时,和我坐对桌的一个老师经常跟我发牢骚:“咱们当老师的吭吭地干,什么好处也得不着。”
他的话是相对于城市老师而言,城市老师有家长恭敬着,也深受社会尊重,乡村老师却不然。我在乡村学校当了5年老师,没有一个家长找过我询问过学生的学习情况,更没有家长请我关照他的孩子。除了工资,老师也没有其他任何报酬。
但我还是很满足,因为他说这话时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了在农村刨冻粪的情景。
我中学毕业后在农村劳动过两年,庄稼地里的活计才叫累呢,通常干一天活儿后,夜里上炕睡觉都费劲。冬天也不得闲,要把生产队里的冻粪刨成一块一块的,用牛车拉到地里,隔一段距离卸一堆儿,等春天种地时冻粪化了,撒在播了种子的垅沟里。
而这刨冻粪和“愚公移山”也差不多了,堆成山一样的冻粪跟铁坨似的,相当坚硬,用尽全身的力气刨一镐下去,人都不由自主 “吭”地吼一声。所以,每刨下来一块冻粪,都需要“吭”无数次,累得人东倒西歪,脑袋汗气腾腾,那才真是打实“吭吭地干”。
教学固然辛苦,早起晚睡,很多的节假日也都用在了备课和批改作业上。可是,再辛苦也达不到“吭吭”的程度。
于是,我问那位同事:“你干过刨冻粪的活计吗?”
他愣了愣,怪怪地看着我,一脸的不解,不知道我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断定他没干过刨冻粪的活计,当然也不知道累到什么程度才算“吭吭”地干。
我从乡村学校调入行政机关当秘书,主要的工作是写材料。我们3个秘书中有一个年龄在50岁左右,对写材料这种工作有抵触情绪。
每次领导布置了写材料的任务,他都嘀咕:“就知道让咱们吭吭地干,什么好处也不想着点咱们。”他说的好处,是在机关写了多年材料而没有提拔过,依然是科员。
我问他:“你刨过冻粪吗?”
他看我一眼,很不满地说:“平白无故我刨那玩意儿干啥!”
我又问:“你没刨过冻粪,看过刨冻粪吗?”
他更不耐烦,说:“我没在农村待过,哪看过那活计?”
乡间有句话,叫做“没吃过肥猪肉,还没看过肥猪走吗”?可他没刨过冻粪也就罢了,都没看过,就难以说服他了。
他把一件与“吭吭”地干毫不沾边的活计理解为“吭吭”地干了,好像受了多大的累,老是抱怨,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也影响了提拔。
就我当秘书的经历,体会到写材料并不累人。动动脑筋,构思个提纲,形成文字,即使为赶会议起早贪黑地写,也达不到“吭吭”的程度。写字不可能像刨冻粪那样,每写一个字都“吭”地吼叫一声。
假如这个秘书刨过冻粪,或者看过刨冻粪,知道累到啥程度才是“吭吭”地干,就不会那样说了,而是会愉快地接受任务,保质、按时完成。那么,他所追求的提拔也许就顺理成章了。

我调到报社当记者,每个月都有写稿任务,多劳多得,但不能应付,因为稿件要分为甲等、乙等、丙等,每个月对达到甲等稿件的数量都做了规定。想完成任务,就得全力投入,认真采写,否则完不成任务。
于是有人就反映说,整天吭吭地干,所花费的力气和收入不成正比,想想都犯愁。
我亲历过“吭吭”地干,那个干法儿,是拼到每个汗毛孔都张开的。写稿件和刨冻粪相比较,远达不到“吭吭”的程度,所以我写稿件从没有“吭吭”地干的感觉,也没因为写稿犯过愁。
从参加工作那天起,我所从事的工作和刨冻粪比,都太闲了。由此我整日心慌意乱,感觉没全力以赴地干工作却拿足了公家给的钱,这不是巧取豪夺么?
要是有二亩地可种,有墙可垛,有一幢房子可盖,有一堆冻粪可刨……可是全没有。
让我奇怪的是,和我一起刨过冻粪的农民,常年累月“吭吭”地干,所得和付出似乎并不匹配,他们倒没有抱怨过太辛苦,没有嫌挣得少。
可能他们来到世上,看到父辈就是在“吭吭”地干,自己有了劳动能力之时也“吭吭”地干,觉得人的一生就是“吭吭”地干吧?
每个人在自己的经历中都或多或少留有深刻印象的东西。而“吭吭”地干,则在我记忆中挥之不去驱赶不走,做什么事,我都不由会想到“吭吭”地干。
有“吭吭”地干的事情做,心里就踏实、愉快;如果没有,心里就发虚,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
而且我认为,人这一生,不论做什么事情,总能有“吭吭”地干的条件,实在是一种幸福。
作者:吕斌
责编:张初 / 校对:郭艳慧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