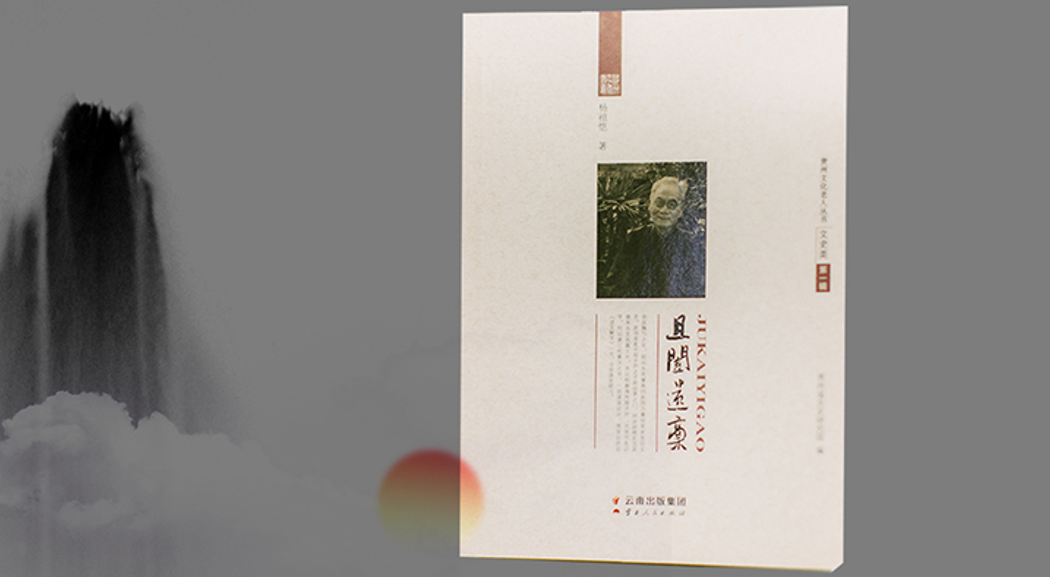
余自舞勺之年,即从乡先辈表伯赵恺乃康师受学先后五年。赵师亲炙于郑子尹之子郑伯更之门,对余讲授史汉及唐宋古文名篇之外,并以程春海传授子尹“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秦汉之书”,一语谆谆训示,授余以许氏《说文解字》一书,令余逐字研习。
——杨祖恺
《贵州省志·地理志》读后
今天编写地方志,无论体例、内容、方法以及科技成果资料的充分利用,都是旧中国时代远远不能比拟的,这就是编写各级新方志的时代特点和物质基础。
贵州省志编委会领导全省的修志工作,除了面对全省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组织落实各级修志机构、充实和提高全省修志工作的队伍等工作之外,还帮助地州市县编出了一批地志或专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贵州省志的编纂工作,也在同步进行,迄今已正式出版的,达七种八册。其中,地理志上下册的字数容量最大,共一百四十余万字,由编委会延聘省内专家学者参加编写和审稿,历时三年始告完成。此书的正式发行,在全国修志界引起相当的注目。下面谈谈个人读本书后的一些认识:

我国的修志工作,源远流长,是长期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而形成的。但是,不论远溯方志的雏形,如先秦的《禹贡》《周官》等书,或是发展到相当成熟阶段的方志,如隋唐宋等朝的图经、地志,还是明清时代定型的省府州县志书,都离不开以一定地区范围内的“地理”作为组成方志的一个重要方面。
清代贵州大儒郑子尹、莫友芝合纂了著称一代的道光《遵义府志》,郑在该书的序例中说:“地理水道,图经之根。批郤导窾,亦夥言頁(读:yín)陈……”。而莫氏谈到贵州修志的甘苦,也说:“方志重沿革,而沿革莫难于贵州,贵州沿革,莫难于乌江以南贵阳诸府……”。可见百余年前他们修志时,对地理志部分,同样是非常重视,但也已感到历史资料的残缺和困难了。
但是,旧时代方志的内容是受当时的社会环境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的。旧方志中的地理部分,诸如地图的测算、绘制,自然地理方面的科学资料以及人文地理学科方面的调查、统计、分析等等,都是远远达不到现代的科技水平的。为此,我们编纂地方志时,既要合理地继承中国历代修志的优良传统,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指导我们的修志工作。正如一九八O年三月,胡乔木同志在重建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的:“地方史要加强研究,地方志的资料要收集,要保存,要研究……我们国家有修地方志的历史传统,今天我们要继承这个传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去编写地方志,这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可见,我们今天修志的条件,比过去优越,但工作的难度和要求,和过去也是不相同的。

《贵州省志·地理志》的编写,是根据上述的原则进行的,粗读以后,我认为有以下的一些特点:
一、从体例的安排看,这部地理志,与过去的方志迥然不同。
明清两代是我国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永乐十六年(1418年)曾颁发了《纂修志书凡例》,规定志书的类目有: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田地、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后来修志,基本多是按这些类目,作了增减分合而已。总的说来,其中如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田地、风俗、户口等的内容,都是和地理有关的类目。再看清代贵州的几部省志,有关地理的篇目所占比重也较大。以乾隆《贵州通志》为例,属于地理范畴的,有星野、气候、祥异、舆图、建置、疆域、形胜、山川、关梁、邮传、风俗、苗蛮等。而民国《贵州通志》的地理方面,则在明、清旧方志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改异。它在卷稿首列有历代疆域图,再设舆地(山脉、水道)、建置(沿革、城池、衙署)两志。
从上比较,旧方志的地理范畴,到今天已经产生了实质的变化。且不说像星野、祥异等篇目的内容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在新方志中不可能再列。就是在民国时期省志中的城池、衙署等门类,也随时代的进步而失去了详细记载的价值。所以,新志中的地理方面,必须有符合时代发展和需要的新篇目,《贵州省志·地理志》的篇目设计,正是在既无可资借鉴的情况下,较早地提出一个崭新的篇目。这个篇目是根据现代地理学科的系统内涵,把贵州省的地理状况及现代地理学科技研究成果作系统的阐述。从上册的人文地理部分分为建置沿革、现行政区、人口、城镇四篇;到下册的自然地理部分的地质矿产、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物和植被动物、自然灾害八篇。这虽是一个在新方志中带有尝试性的地理志篇目,但它能在全国范围内较早的提出并编印出版,从地理科学的角度,通过地方志的形式,较全面地介绍贵州全省的省情和地情,则是极为可贵,值得欢迎的。
二、这部地理志的资料,充分利用了现代地理科学的较新研究成果。
因此,它的内容,既要求通贯古今,又必须展示现代科技的最新研究成果。这部专志的上册,从人文地理角度,概述了贵州建行省以来六百年的基本情况。至于建省以前的贵州疆域、设置,上起周秦,下及唐、宋、元,首因历史资料的断缺不全,再有若干举世瞩目的重大史实,如鬼方、夜郎等的地望,唐宋经制州、羁縻州等设置原委等,学术界尚多歧义,故只作简略扼要的介绍,这是符合方志“详今略古”“记述为主”的普通原则的。下册的自然地理方面,则是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各方面专家学者对贵州地情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大量资料,系统编述。就资料言,既丰富又翔实,价值是很大的。
三、《贵州省志·地理志》是结合了若干专业部门的专家学者分别执笔编纂成书的,体现了众手修志的时代特点。
因为地理志牵涉地理学科的门类较多,特别如像人口、地图测绘、地质、地矿、气候、水文,土壤、动物、植物等等,专业性较强,还有涉及全省地州市县的一些基本情况。故本书的编成,依靠了若干学科的专业学者共同拟定篇目、收集资料、撰写初稿,再聘请我省一些著名的老专家学者参加审定。特别是编委会,在秦天真主任的亲自领导下,几次开会,认真审稿,对本志的提高水平,保证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读了这部地理志之后,不禁又联想到在编写新方志中,还有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思考和探讨的一些问题。
首先,方志内容的科学性和文字的可读性应如何统一和结合。因为方志是一部综合地方各个门类知识的“百科全书”。编写方志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资治、存史、教化”的资料汇集,它和专门性质的学术性著作又有所不同。如果它所记述的内容只是限于专业的教科书那样的理论知识,那么,纵然是很系统、很全面的科学技术资料,恐怕仍不能很好地起到资治或存史的作用。何况各种专门知识对于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来说,是比较难于接受的。所以,方志应该在尽量不损害专业知识的完整性原则下,又能努力在文字上的深入浅出、叙述条理生动方面多下功夫,以加强志书的可读性。使一些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篇章,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做到科学性与可读性的结合,恐怕是新志书编写中一个应该重视的问题。
其次,本志分为上下册出版,但出版时间前后隔了近三年(1985年12月至1988年8月)。上册以历史资料为主,下册以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等为主,上下册各冠以凡例,因此通读上下册以后,感到有点不太贯气。这样安排凡例,不免使全志的统一性受到一些影响,这就会使我们联想到一部完整的省志,是采用多种专志又多卷出版的,时间跨度相当长。
如何才能使一部志书既能前后一致,保持全书的完整性,又能照顾各个专业志的特殊情况,使后来者赶超过去,不断提高质量,这也是应该好好考虑的。
总之,这部“地理志”的成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还是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或是预见性不够,而出现不足之处。这次省地协召开的评稿座谈会,就是希望通过修志同行的讨论,为今后省志专志的编写出版,提出一些可供借鉴的参考意见,使志书的质量,不断改进和提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谨以一得之见,就正于修志界同仁。

杨祖恺(1915-2010),出生于贵州遵义 ,精于隶篆,省内名胜古迹均有墨迹存世。1980 年后参加地方史志编纂、古籍整理等工作,曾任贵州地方志编委会特约编纂、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等职,1985 年受聘省文史馆馆员。出版有诗词联文合集《将就斋杂稿 》,遗著有《且闿遗稿》。
(来源: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