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路走一路看,从乡村到城市,从山岭到海洋,
大千世界,入目入心。
我沐浴着八面来风,吸收着多种营养,
但还是保留着老地瓜秧的秉性,
忘不了自己的卑微出身,
一回到家乡的土地上就感到踏实、舒畅。
过去,地瓜是鲁东南一带老百姓的主食,大部分土地用来秧地瓜。秧,在这里是名词用作动词。人们用犁扶起一道道地瓜垄,然后手捏秧苗,抠出土窝栽上,再浇一点水,它就扎根生长。那些根,有的慢慢变粗变大,成为地瓜。
凭空结出一个个地瓜,需要好多养分,光靠根须吸收远远不够,还要靠秧子帮忙。它长出许多叶子接受阳光,还从垄顶爬到沟底,生出一些不定根,从这里汲取肥料,而后再向相邻的地瓜垄登攀,秧尖昂扬,企图再去另一个沟底。秧子上一旦生出不定根,可能长成指头大的小地瓜,消耗和分散养分,所以人们在夏天要经常翻地瓜秧,将它翻到瓜垄的另一边。地瓜秧暂时悬空,过几天它还会下沉地表,再生出根来,秧尖也会在另一个方向继续前进。因此,在地瓜秧生长的旺盛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翻它们一次。
一
小时候,我对地瓜秧的这一习性十分好奇,多次蹲在地瓜沟里仔细观察,看它多么努力多么倔强。我想,如果不翻秧,放任不管,它大概就会一直长,一直长,长到地外边,翻山越岭。我那时只去过六里远的公社驻地,很想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我白日做梦,恍惚间觉得自己变成一根地瓜秧,嗖嗖地长,拖拖拉拉,到处扎根,四处观望。
地瓜秧被人翻来翻去,终其一生,也只能移动两三米。本来,它的生长期应该和地瓜一样长,但那个年代地瓜产量低,一亩只收一两千斤,不足以填充人的肚子,只好提前割秧救急。我们那儿把这叫做“捽地瓜头子”,大约在收地瓜之前半个月左右。生产队统一组织,指定地块,让妇女和小孩拿捽刀割。稍嫩一点的前半截秧子被捽下,留下已经老了的后半截,断茬处滴着液泪,继续陪伴土里的地瓜。地瓜秧还不能多捽,按各家人口数量定个限额,临走时队长过秤,会计记账。妇女们把地瓜秧背回去切碎,或者马上吃,或者晒干了长期保存。在那些秋高气爽的日子,麦场上,院子里,街两旁,都晒满了绿生生的地瓜秧碎屑。它晒干了没有分量,大风一刮容易飞走,所以要围一圈茓子挡住。
初秋捽地瓜头子,成为一个惯例。家里有个地瓜头子囤,也成为庄户人家的标配。
地瓜头子囤的旁边,一般还有个糠囤。收完地瓜,人们将地瓜秧也收走晒干,将上面残留的叶子抖落下来,用碌碡压碎装进囤里。后来生产队有了粉碎机,干脆把地瓜秧连梗带叶都打成糠。这些糠,一般用于喂猪,饥荒年头也拿它喂人。
以地瓜为主食的年代虽然难熬,但有一些场景、一些经历还是给我留下了美好回忆。
集体翻地瓜秧的经历,让我经常回想。一群人斜排成阵,每人负责一垄。人手一根长木杆,尖头都被沙土磨得很锐利,像冷兵器时代的长矛。顺着地瓜沟往前一插,再一挑,青翠的地瓜秧嗖嗖翻飞,去了地瓜垄的另一边。这时,常有蚂蚱和螳螂惊惶逃跑,或跳或飞,我们就去追去逮。逮住后取下头上的苇笠,用苇笠边缘的细麻绳将它压住。收工时,每个人的苇笠上都是满满的一圈,如果更多,则用狗尾巴草穿成串拴在苇笠上。回家炒熟,便是一盘香喷喷的“就食”(下饭菜)。
三伏天里,地瓜秧长势最旺,每一个叶子都由叶柄托举着,向着天空全面展开,表达它们对太阳的爱意。休息时,有些小姑娘常常用它做耳坠:采下叶子,掐掉叶片,将叶柄擗开,往左掰一下,往右掰一下。擗到底掰完了,由表皮连缀成一个长串。那个时代不许女性戴首饰,她们将这种坠子搭在自己的耳朵上,轻轻摇头,颇具风韵。我学会了,独处时也曾做过几条,却不知道给谁戴。这个手艺,从此荒废。
还有深秋晒地瓜干的场景。那时收下地瓜,除了装窖用作地瓜种并随时吃,大部分要晒成地瓜干储存起来。虽然要用“抢子”把一个个地瓜切成薄片,要把地瓜片子撒在地里均匀摊开,如果来了雨还要急急忙忙抢收,整个过程很辛苦很劳累,但那些在太阳下晾晒的地瓜干漫山遍野,像天上落下的一片片白云,还是让人心醉神迷。
1981年春天,我们公社在全县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正担任党委秘书,整天跟着书记往各村跑,一人骑一辆自行车。看着父老乡亲发自内心的欢乐,突然爆发出的劳动热情,我觉得这个春天实在是太美了。到了秋天更美,家家户户都收了好多地瓜,晒的地瓜干子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土地。那时我已结婚,老婆孩子是农村户口,也分到了责任田。我有空便回家帮忙,秋后收的地瓜也不少,地瓜干子装了满满一囤。
不过,后来因为地瓜,我也遇过挫折出过丑。
二
我当秘书时已经开始业余创作,丰收的地瓜敲击着我的神经,让我产生了用小说记录农村变化的念头。每天忙完公事已是晚上八九点,我却精神抖擞,躲在宿舍里挥笔苦干。从秋天开始,我用半年写出一个十万字的中篇小说,叫作《在那冶红妖翠的河边》。可惜我那时眼界太窄,感受太浅,像一根嫩地瓜秧,只看到当时的冶红妖翠、风调雨顺,没体察到大地上的历史积淀之久之深。再加上功力不够,笔法幼稚,写完寄出去,很快被退稿。这个打击让我难以承受,头发大量脱落,不只出现家乡人说的“疤顶”,脑后还有两块明晃晃的斑秃。
第二年,我希望我家能收获更多的地瓜,特别注意学习“科学种田”经验。看到报纸上介绍了一个高产做法“一炮轰”,就回家和老婆如法炮制。所谓“一炮轰”,就是栽秧时捏一些化肥直接放进苗窝,而不是等到瓜秧长起之后再追肥。没过几天,老婆跑到公社气呼呼向我报告:地瓜苗都叫化肥烧死了!我急忙跟她回去看,果然如此。老婆的责任田里,秧苗全都焦干,而在相邻地块,别人家的秧苗长势甚旺,已经歪下梢尖,准备向沟底进发。父亲来到地头向我瞪眼:阖宋家沟没有不知道你这“一炮轰”的,都笑话你!
我百思不得其解,“一炮轰”是报上登的先进经验,怎么到我这里就失败了,让我成为全村人炮轰的对象呢?看来,白纸黑字不能全信。沮丧之余,我只好和家人一起重新栽秧。因为误了农时,瓜秧就短,结的地瓜也少。刨完地瓜切晒时,我既劳累又自卑,手指头还突然顶到刀刃上,割开一道口子,鲜血涌流。我捏住伤口坐到一边,看到被薅掉的地瓜秧已经蔫了,却有一根没被薅下的地瓜秧还在高高翘头,望向远方。我突然觉得,它就是我。它想走出去,不想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不想在这里一代一代繁衍,却都是土生土长的地瓜。我暗下决心,要刻苦努力,让自己有资格带老婆孩子离开农村。
一年后,我写公文的能力被县委办公室的领导发现,便到那里当了秘书。我一边工作,一边在业余时间读电大,农忙时还要回家种地。有一天我像牲口一样拉耙时,心里想起海德格尔的名言“诗意地栖居”,不由得泪洒墒沟。
又过了一年,我决定把家搬到县城。老婆嘟哝道:“进了城不种地了,吃什么呀?”我说:“放心,饿不死你!”
虽然饿不死,但生活十分拮据。有一回老婆告诉我,她带女儿上街,女儿从街边捡起一块橘子皮,举到她面前说:“你闻闻,真好闻!”我这才意识到,平时很少买水果给孩子吃。更让我受伤的是,孩子到了上学的岁数,我送她到离家最近的一所小学,竟然因为农村户口报不上名,人家只收城镇户口的孩子。我低三下四求人,才把孩子送进去。这时我才明白,我虽然进了城,却还是一根地瓜秧,老根还在离城四十里的山沟里。
三
这根地瓜秧偏偏不安分,还想向更远的地方延伸,三十三岁那年决定改行,考入山东大学作家班读书。为了写好作品,我一门心思向远处看,看当时的文学思潮,看外国的作家作品,开眼界,长见识。我东施效颦,见样学样,不是写着写着难以为继,就是写出之后被编辑退稿。那段时间我非常痛苦,颓萎不堪,像地瓜秧遭了严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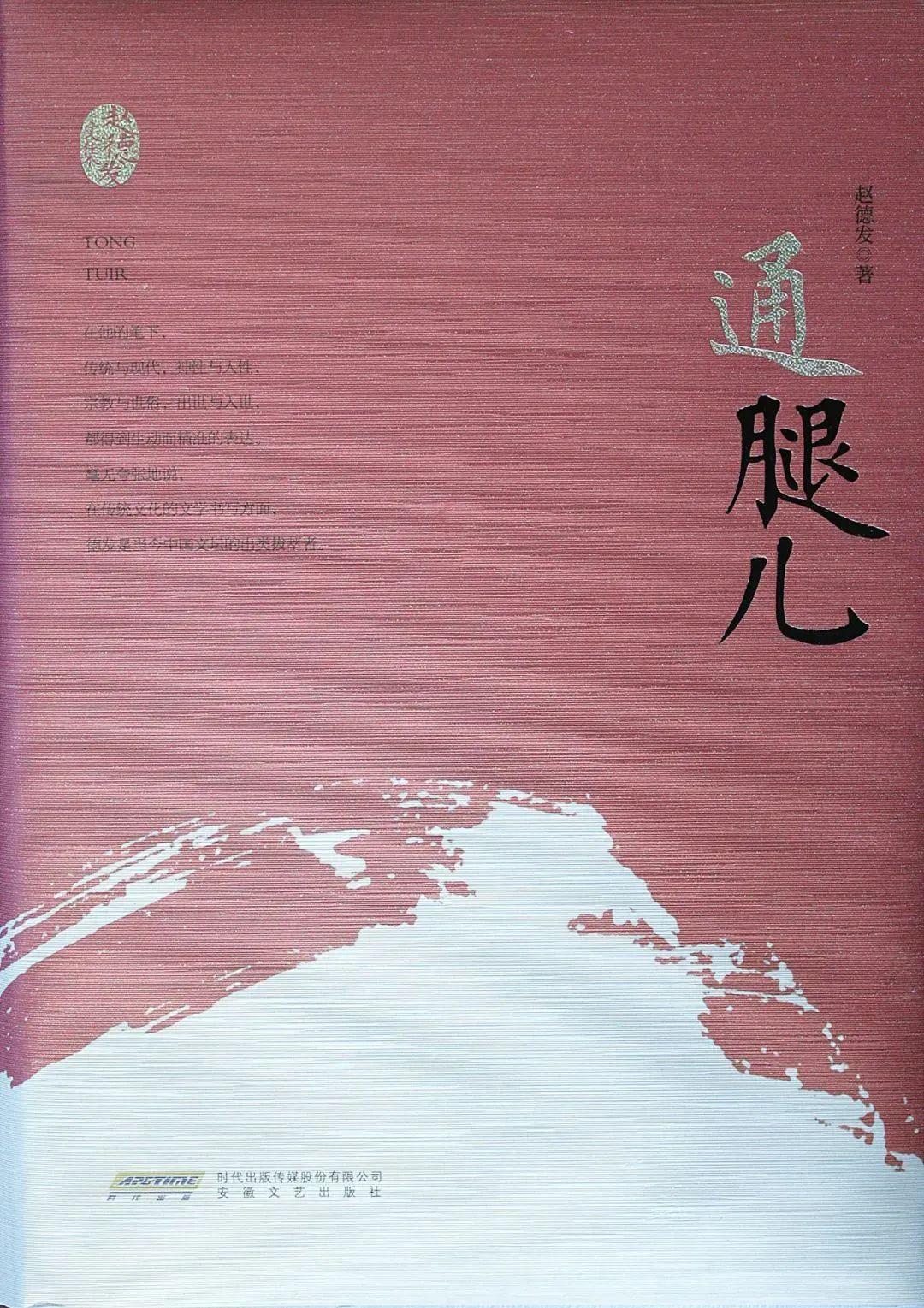
不过,童年记忆中的地瓜秧又鲜活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它那倔强的样子、奋进的姿态让我重新振作。我在大学里汲取营养,拼命读书,回望家乡,憬然有悟。暑假中我回老家看望父母,帮他们下地翻地瓜秧。看到秧子长得正旺,妻子十分兴奋,立即捽了好多,要带回县城吃。我看到长长的地瓜秧,突然想到我们村早年走出去的几位前辈,都是早早参加革命,后来成了南下干部。我姥爷牺牲在河南,另外几个活了下来,有好多故事在乡间流传。我脑子里灵光一闪,有了一个构思。这个构思,过几天落到纸上成为短篇小说《通腿儿》,发表后获得好评,让我爬上了写作道路上重要的一个台阶。
我在山大两年,毕业后到日照市工作。虽然离老家二百里,但我感觉自己还是一根地瓜秧,根系家乡,魂牵梦绕,经常回去看看。我看家乡时,就像地瓜秧吸收了多种养分,视角与从前不同,有了许多新的发现、新的认知,力求在作品中表达出来。我写了许多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跨世纪前后又完成了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总名为“农民三部曲”的这几部作品,表现农村百年巨变,并写出了一个大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正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思维方式、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都在改变的一代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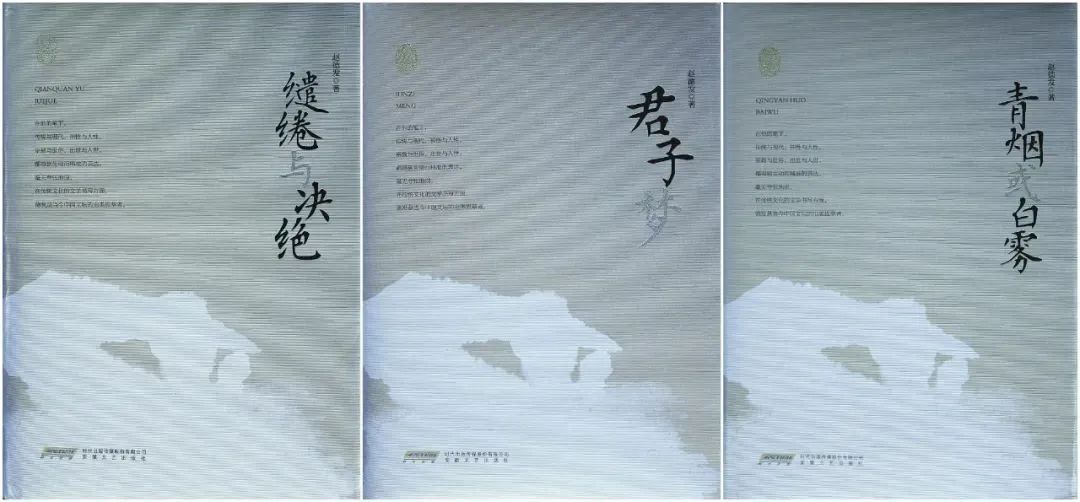
土地充满生机,故事层出不穷。我家乡的岭地大多用来秧地瓜,有些平原地区却种大蒜,“蒜你狠”“蒜你贱”的悲喜剧经常上演。2011年,我认识了一位被人称作“蒜神”的远房亲戚,跟着他到鲁南苏北多处蒜区转悠,听说了好多传奇故事,了解了蒜农、蒜商的甘苦。走进蒜田,看着一根根蒜薹,我觉得它与地瓜秧十分相似,都维系着栽种者的生活,牵连着他们的命运,便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与大蒜相关的故事。第二年春天动笔,刚写了几万字,我那位亲戚却因为他担任副总裁的大蒜电子盘崩盘而被捕,获刑十年。我两次去盐城旁听案情后,决定不写小说了,写一部长篇纪实文学。2012年年底,我踏着黄淮平原上的积雪去“蒜都”金乡县采访。第二年蒜收季节又去另一个大蒜产区邳州,接触到许多蒜商、蒜农,听他们讲述大蒜如何成为“白老虎”屡屡伤人,与他们探讨应对措施。最终,我写出《白老虎——中国大蒜行业内幕揭秘》,被许多读者尤其是蒜农、蒜商传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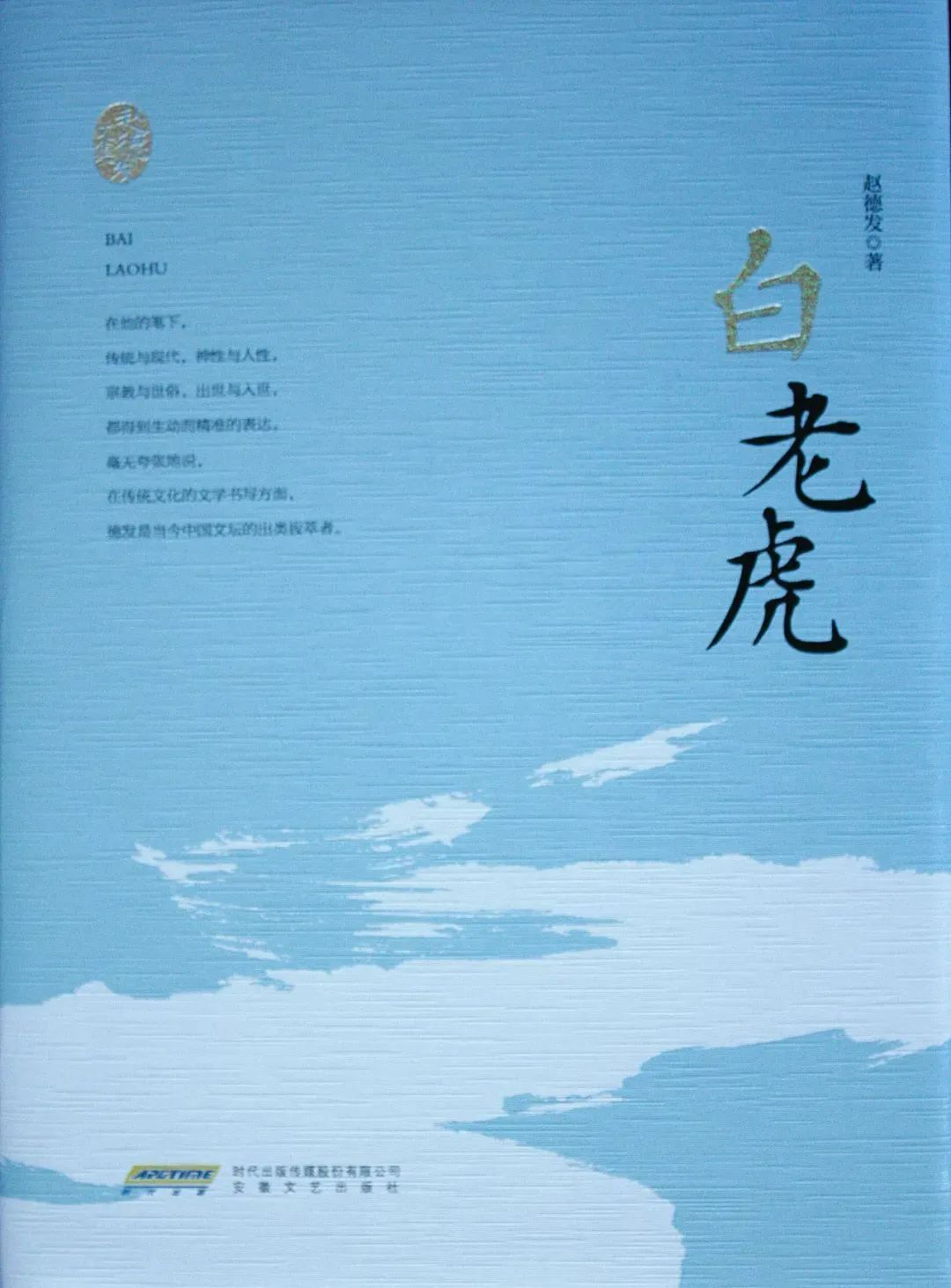
日照在黄海之滨,有传承已久的渔业文化,有在中国航运业居重要地位的大港。我对海洋文明的了解日渐加深,同时也以海洋文明的视角观照农耕文明。就像一根从山地爬来的老地瓜秧,在海边东看西望,做着比较。对自己的根,我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也能以新的历史观、文明观做出研判。我在201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经山海》,特意安排主人公吴小蒿出生于农村,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让她具有异于常人的历史眼光,对她任职的海边乡镇和渔村、海岛,对她与同事们投身其中的乡村振兴大业,都有深刻的理解。

四
近年来,中国乡村变化巨大,体现在方方面面。我利用各种机会四处游走,在全国看了许多地方。

我几次去新疆,感受特别深。1999年我去南疆时,看到家家户户只靠一辆驴车拉庄稼、赶巴扎,而去年我和文友夏立君应日照援疆指挥部的邀请去讲课,看到好多人家门前都停着小汽车。欣赏着刀郎木卡姆,看着演唱者们发自内心的喜悦,我深受感染。前年我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去北疆,看到政府主导的许多产业让当地人脱贫致富,改变了生活。有一些村庄,薰衣草、红花的旁边便是漂亮的民宿。一天傍晚,我们在一户人家的楼顶坐着地毯看夕阳,嗅着花香与主人说话。他讲,种了几年的薰衣草,好多人家的存款都有几十万、上百万,说着说着便兴奋地唱了起来。在塔城裕民县的一个村庄,我竟然遇见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移民的老乡。他来自沂蒙山区,因为家乡穷,听说这里地多人少,就到了八千里之外的这里定居。现在他是种粮大户,有好几台大型农机。他特意与我在拖拉机旁边合影留念,那个大轱辘,差不多与我等高。说起当年在老家吃地瓜秧,吃“棵棵子”(野菜树叶之类),他不胜感慨。我告诉他,咱们的家乡,早已变了模样,他笑着点头:知道,我回去看过。
的确,过去的沂蒙山区、鲁中山区,一直与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现在早已甩掉了这两顶帽子,富了起来。富起来之后,还致力于精神脱贫、文化振兴。这几年我去过一些地方,亲眼目睹了这些变化。
在沂河源头,一处处青山绿水被赋予文化内涵。沂源县鲁村镇的龙子湖畔,竟然建起了桃花岛文化艺术乡村。几个村子的闲置住宅被利用、被改造,先后建成二十多家文学馆、艺术馆、博物馆,成为旅游胜地和研学基地。好多村民,成了这些艺术馆的建设者、管理者、讲解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艺术活化乡村,文化浸润田园”,从理想变成现实。我前年去参加刘玉堂文学馆开馆仪式,今年9月份又去参加于希宁艺术馆、王音璇艺术馆、山东大学作家班文学馆等六个馆的开馆仪式,沉浸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之中。据了解,桃花岛文化艺术乡村的艺术馆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争取达到上百座,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五彩斑斓的馆群。这里,还挂起了“山东财经大学乡村振兴学院”的大牌子,频频举办与乡村振兴有关的培训班、研讨会及多种活动,成为一所建在乡村大地上没有围墙的大学。一些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甚至两院院士经常来此,为乡村振兴贡献智慧。
从这里往南走,在沂河右岸,位于沂南县岸堤镇的朱家林田园综合体让我有惊艳之感。一座座漂亮的民宿、展馆、体验馆、创客公寓,各具特色的创意农业区、田园社区、电商物流区、滨水度假区、山地运动区,让4万多亩山地变成了三美(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乐园,广大村民过上了“半农半X”的生活。所谓“半农半X”,就是一部分时间从事农业,其余时间发挥特长或根据需要从事别的行业,获得更多收入,并实现个人价值。譬如说,在社区中心的非遗展馆,有许多本地女性在那里向游客展示各种传统手艺,做剪纸、捏泥哨、糊灯笼、纳鞋垫等等,有的还守着鏊子教大家烙煎饼。晚上,有些年轻人和游客一起参加“我把田园唱给你听”草坪音乐会,满怀激情一展歌喉。
我在挂满金黄柿子的树下看到一个牌子,写有“理想村”三字,心想,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著作中构建了一个“理想国”,成为近代“乌托邦”思想的源头,而这里的“理想村”却实实在在,成为国家级田园综合体、乡村振兴样板。我向同行者感叹:老乡们越来越大气,越来越时尚,越来越浪漫。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这里现出端倪。
五
沿着沂河再往下走,就是临沂。从临沂往东四十公里,是我的家乡。到这里走走,遍地薯香,让我格外亲切。过去鲁东南各地广泛栽种地瓜,但近年来因地制宜,调整生产结构,发展二三产业,这种作物越来越少。而莒南县南部因为土壤适宜,种植面积却不减反增。我的家乡相沟镇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薯香小镇”,大部分土地栽种地瓜,商家收购后运往上海、南京、青岛等大城市。更让人赞叹的是,家乡人还在红薯文化上大做文章,建起了一座红薯文化展馆,多次举办红薯文化节。许多乡亲在网上做直播,有的年轻人还会用时尚语言、艺术手段卖地瓜,让天南地北的消费者纷纷下单。
乡亲们告诉我,今年秧的地瓜,无论产量还是价格,都比去年更高。有的品种亩产六千多斤,在地头就卖,能卖四五千元。如果放到窖子里储存,春节前出货,还能进一步增值。有人通过土地流转,秧一百多亩地瓜,能挣几十万元。
我看到,地瓜收走了,地瓜秧却被随随便便扔在地里。问一个年轻人,怎么不拉回去,他说,自己不养猪,不用它做饲料,做饭用液化气,也不用它做柴火,拉回去也没有用。扔在这里,有的养殖场会拉走做饲料,一亩地给四十块钱。如果没人来收,也就不管了。
我拿起一把地瓜秧看看,它们一根一根都很短,秧子上也没有不定根。我早就知道,现在的地瓜早就不是过去的品种,已更新换代无数次。新品种的秧子短,不用翻秧。我问年轻人,现在还有没有人捽地瓜头子吃,他笑一笑:“都什么年代了?除了一些老年人偶尔吃一回,年轻人没有吃它的。”
我手扯一根地瓜秧,想我六十多年的经历与见闻。我一路走一路看,从乡村到城市,从山岭到海洋,大千世界,入目入心。我沐浴着八面来风,吸收着多种营养,但还是保留着老地瓜秧的秉性,忘不了自己的卑微出身,一回到家乡的土地上就感到踏实、舒畅。

一家三口在老家。
抬头望向西北方向,似乎看到了一座高塔。那是我在朱家林村头看过的“再生之塔”。它是一座方形碑,由钢筋混凝土筑起,表皮却用乡村废旧材料拼贴而成,如拆下来的老门板、旧砖瓦、藤编、山草等等,象征着朱家林的涅槃重生。
我想,如果在我家乡也建一座“再生之塔”,除了那些老的物品,一定要放上地瓜秧,让它们攀援而上,为乡村巨变作证。
作者:赵德发
来源:农民日报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