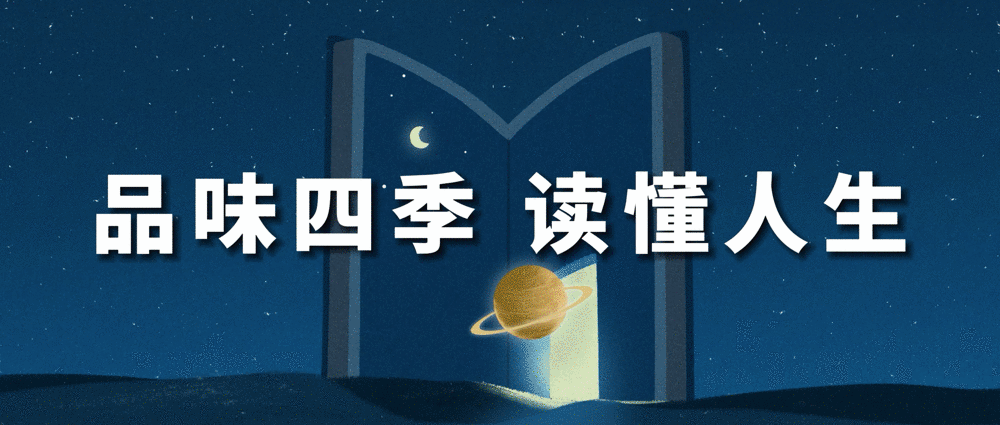
头3个月,我天天去泡图书馆。那些日子,真正体会到了文字的非凡魔力——它可助人将痛苦彻底抛之脑后。
最初是没心没肺地阅读,图书、杂志、报纸,随手翻。感觉乏味的放下,若能让眼睛一亮的即找个地方落坐静读。但是到了夜晚,听着寝室同学的鼾声,我依然会偷偷擦泪。心是真的痛。失落、沮丧、惘然、哀怨……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伤痛,也真算不上天大一般。只是年少,便放大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折。
那是与高考录取有关的痛。
我在1991年参考高考,是那所乡村中学的文科生里唯一超过重点线的幸运儿。但最后拿到录取通知书,却是一所中专学校。
据说学校的前世是兵工厂,所以选址较为偏僻。其实学校风景不错,群山环绕,还有一个水库相依。只是我那时内心灰暗,万物入眼均难生辉。入校之初,我不愿亲近同窗,独来独往在图书馆里亲近文字,成了稀释痛苦的法宝。
有天晚饭后,我又去了图书馆。胡乱翻看杂志时,3个字跃入眼中——“找笔友”。漫不经心扫眼过去,有个叫“陆贺赟”的名字让我停驻良久。“贝”上站个“斌”,读作啥?我马上查字典。赟:美好之意。
陆贺赟,应该是父亲姓陆,母亲姓贺吧?我猜测着。名字旁边还有个女生的照片,很漂亮,和名字一样美。我决定给这个远在浙江的陆贺赟写信,交个笔友。

第一封写给笔友的信,究竟什么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但几个细节倒是没忘。比如,信封上的地址、姓名,我悄悄“露了一手”,用的是隶书;信内则间或正楷和行书之间,用的是自创字体。邮票呢,也不是学校小卖店能买到那种常见的,而是从我的集邮册里拣出一枚余出的纪念邮票——我不想该信件被读后揉成一团坠入垃圾桶,有去无回。我希望收到回信。
一个星期过去,果然收到了回信。而且,陆贺赟的书写果真娟秀。
自那以后,我和求学于西子湖畔、家在舟山群岛的女生陆贺赟成了笔友,隔些天必有鸿雁传书。
我向未曾谋面的陆贺赟诉过苦,讲述自己高考录取不公带来的苦闷和失落。收到她的热情劝慰,我立马感受到了春暖花开。
我生在湘中的小山村,20岁之前连火车都没见过,更别提浩瀚的湖海。陆贺赟向我描绘着她的家乡舟山群岛,我眼前便浮上波澜壮阔的苍茫。她还替大海向我发出了召唤:来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你飞……
而我生命的航向,却突然间转了弯。
先是参加班干竞选,很快出任班长;接着,又拉起校文学社队伍,并担任了校刊主编;还操持了学校广播站的工作人员配置,以及在校长钦点下组建了学生会办公室……短短两年,除最初的那3个月,余下的光阴再不曾虚度。毕业离校时,我已确定了奔赴特区的奋斗方向。
这期间,由笔友生发的纸上的友谊是弥足珍贵的。当我跌倒,它予以了我心灵慰藉;当我彷徨,它旁敲侧击促我警醒;当我奔跑,它同样兴高采烈地分享了我的欢欣。这些,我的笔友陆贺赟都做到了。

读中专时,我其实还有另一位“笔友”。
有个与我高中同窗但没说过一句话的女生,曾是我最好的哥们先暗恋后公开恋爱的女孩,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师大就读。哥们到古巴陵郡求学,见我俩都在长沙,遂拜托我照顾她。可是,该怎么照顾呢?她又不是3岁娃。不然,就写几封信算作送个温暖吧。可是通信不似面对面聊天,本无声无色。要写,就得写出个味道。该女生被录取进入大学,我却只读个中专,由此心生自卑。担心写信水平太低被她看扁,所以每每写信,我都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力争超水平发挥。
我们同窗时没说过话,印象中的她不苟言笑。而收到回信,我情不自禁笑了。纸上的她,竟是酣畅淋漓的女侠。读她的信,如骄阳酷暑下手里捏着个爽透的冰激凌。她的信末留名是“冰菁”——我知道这不是她的真名,而是与我通信的专用“笔名”。也许专业所读中文系的缘故,冰菁读了许多文学书籍。她钟爱苏东坡,评点张爱玲,言语间文采飞扬,让我汗颜。
有段时间,几乎每周我都会发出去一封信,不是寄往杭州,就是寄往岳麓山。其实,坐校车走一段路,就能直达湖南师大。但写信,更让我着迷。
冰菁对写信也情有独钟。有两次上午刚收到她的来信,下午竟又收到一封,说上一封意犹未尽,忍不住再修书一封作补充。
后来,我走出校园到了深圳扎下根,冰菁也结婚生子;再后来,等到手机短信风行,我和她还会通信。真是友谊长青的好笔友。
前些年的一次老同学聚会,我告诉冰菁,在我老家箱底,竟翻到她厚厚一摞信,读来宛如昨日。她眼睛一红,无语。
人世间流逝得最快而又最无情的,是时光。回头望去,30年光阴已逝。当年托付于邮差传递的字里行间,究竟流淌着哪些细枝末节的喜乐哀怒?我遗憾自己仅记住了十之一二。而我那曾经的最佳笔友“陆贺赟”,如今会在哪里?也不知早已人到中年的我,若给8000公里之外的冰菁再手书一封,还能不能收到回信?



文:蔡半山
来源:《品读》2022年第6期
责编:张初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