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茂斌


(三)
自然界的力量是巨大的,人类社会的力量同样是巨大的,倘若二者叠加在一起,马上就会给世界以新的气象。
进入腊月,飘飘洒洒的大雪,很快就把一座大山妆扮成了一个银色的世界。而与此同时,村子里的每一堵墙壁上都写上了朱红色的标语口号,包括家家户户的门窗、窑洞腿、大门洞、柴草房也全部涂成了朱红颜色。
大山前所未有地呈现出了两种对比强烈的色调:白色的远山和红色的近村。远山“银妆素裹,分外妖娆”,近村“祖国江山一片红,红心向党表忠心”。再还有比这更美丽的画卷吗?真是匠心独运、浑然天成!
当然,白色的世界那纯粹是老天爷的手艺,而那红色世界则绝对是父亲的功劳。
谁能写了那种趴墙的毛笔大字呢?只有父亲一人。不,说准确些,那不是毛笔大字,而是锅刷子大字。因为写那些有一米或几米见方的大字,在整个大山里怎么也找不到那么大的毛笔了。他让队长到各家各户要锅刷子去了,不大工夫,长的短的粗的细的圆的扁的柴的草的各种各样的锅刷子就找来了一大堆。所以墙面上的那些大字全部是用锅刷子写出来的。父亲说那种用柴草捆扎成的锅刷子刷起锅来还可以,而写起字来实在是不怎么样,既不含墨又不经用,仅学校墙上那个“毛主席万岁”就用烂了三个锅刷子。
天那么冷,父亲一写就是半个月,光锅刷子就用坏了五十多把,直写得他双手冻出脓疮,才把“江山”搞成了“一片红”。
当然,不光写大字,也写了很多小字。比如大队墙上的“老三篇”和家家户户门口的语录牌就是用毛笔写的,而不是用锅刷子刷的。
很遗憾,父亲此生学下的文化就用了那么短短的两次。本来能写了漂亮的文章,县委书记还想请他“出山”呢,可是他只伺候了几年公社书记就索性跑回大山掏坡去了。父亲写的一手好字,像柳体更似颜体,间或还有王羲之父子的风韵。可是除了平时山里的人们请去写些契约、记些礼账、过年时写几天对联外,再就没有什么用途了。这一年,村子里的各种墙壁包括土墙石墙砖头墙白灰墙,总算给了父亲一块用武之地。尽管天是那样的寒冷笔又是那样的僵硬(锅刷子是没有什么弹性的),但其端庄而又洒脱的行楷大字还是让那座大山赞赏和品评了十多年。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大姐和大哥从中学返回了大山。像两年前一样,他们依旧穿着破衣烂衫背着单薄的铺盖卷儿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只是方向不同罢了。
“文化革命”中断了他们的学业。在整个三岔中学的校园里,论穿戴恐怕没有比他们更差的了。可是论成绩,能比上他们的人并不多。放在正常的年份,他们考个学校应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而且父母亲也早已表过态,如果大姐和大哥有机会再往上念,家里就是顶上命也会供给的。父亲当年放弃工作跑回山里掏坡,不就是为了让子女们能活出个人模样来吗?
现在大哥和大姐的念书中断了,接下来还会中断一些什么?世事难料,父母惴惴不安。
“回来就回来吧,这是天年在作孽,百姓奈何不了。况且天塌放大家哩。”父亲经常用这样的话来安慰着自己也安慰着这个家庭。
大姐和大哥很快参加了村里的劳动。
大姐和大哥回来以后,从表面上看,给家中增加了两个劳动力,似乎以后的日子会好过些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来是家中的自留地、小块地、掏坡地统统不让个人耕种了。要知道,这些地是那些年全家人吃饭的主要来源,甚至可以说是全家人生存的命脉所在。不让种地,无异于不让人活了。二来是家中的劳力增长速度远远落在了人口增长速度的后面。大姐、大哥是当劳动力了,这不假,可一大群只能吃饭不会劳动的孩子又相继来到了这个家庭。那个时期我们家庭像整个中国一样正处于人口的急剧增长时期。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为世界瞩目,而我们家的速度又为中国人叹为观止,没几年工夫就整整地翻了一番。村上的人们十分佩服母亲的生育能力,虽然在那样一个营养匮乏的年代,母亲的生育速度还是有增无减。到六七年,我们的姊妹弟兄已达到了八个(当然这还不包括母亲肚里正怀着的六弟、更不会包括两年以后又出生的七弟)之多。即使大姐大哥成为了劳动力,但人口和劳力还是相当不成比例。三来是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国家对家禽家畜却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一项滑稽可笑的政策居然堂而皇之地诞生在了中国大地上,这让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中国人大惊失色,让每一个外国佬听后定会笑破肚皮。和我们今天的计划生育完全一样,养猪养鸡都得有上面的指标,得有上面发给你的“准生证”,否则你就是“计划外生育”,会受到严厉的处罚。那种处罚,远比后来的人口超生要厉害得多。现在人口超生顶多是经济处罚或者不给你上户,而那时超养了猪或鸡,首先给你戴上一顶又一顶的政治帽子——新生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然后再开你的批斗会把你拉去游街示众……如此反复折腾,看你受了受不了。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公社党委给村里下拨几个指标,就得按几个指标来养猪养鸡,循规蹈矩,绝对不能超生超育。也许有的人觉得山高皇帝远的,打些埋伏,上头也没有人会知道。但我告诉你,那是绝对不行的,纸里包不住火,谁敢拿自己的乌纱开玩笑啊。公社和大队的干部三天两头就带着民兵小分队拿着木棍来圪搅你的猪圈和鸡窝子,谁敢以身试法?我记得,公社每年给村子里下拨的猪指标是二十来个、鸡指标是一百来个。这就是说每三户人家可养一头猪,每户人家只能养两只鸡。而且这些养大的猪和鸡,得以绝对的低价交给国家(叫“爱国猪”和“爱国鸡”),绝对不让你随意屠宰和变卖。养猪养鸡,向来是山民们解决零花的主要手段,现在这个手也被断掉了。
有这三条理由就够了。读者可以放开胆子去想象那时农民的生存状态。
就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二姐、我、三弟、四弟都陆续上了小学。其实学校里收的费用相当有限,把书费、学费、杂费加在一块儿,每年每个学生也就是三五块钱吧。可就这三五块钱,也没个寻处。真是一文钱能逼倒英雄汉啊!大姐大哥上学时,家里日子紧是紧,但养上一头猪十多只鸡总还可以把这些费用勉强解决了。而现在,没那买卖了!
坡不能掏,猪不能喂,鸡不能养,可是孩子们的学总还得上哩。父亲昼夜不停地思谋着还有啥弄法。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想总比不想要强,有好多事情看似“山重水复”了,可经父亲这么一想,就又“柳暗花明”了,几十年都是这样,所以父亲每逢难事大事必去苦思冥想。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想着想着,父亲终于眼前一亮,把眼睛就死死地盯在了柜顶上那些刚刚领回来的布票和棉花票上——好像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纸就是风景优美的“又一村”。
那个年代,物资短缺,什么东西都是凭票供应。我记得国家每年年初都要发给农民一定数量的布票和棉花票(布票每人每年是六尺还是八尺?记不清了。棉花票八两则是没问题的),让农民再花上平价的钱去供销社购买。往年,发给家中的这些票证,几乎全白白地给了别人。当然也不能算是白给,实际上是一种交换。到秋天分粮的时候,我们家因为人口多劳力少,挣下的工分不够打粮款。这就需要和工分多的户子商量,让人家给拨兑过工分来才能把粮食分回来。至于欠下对方的工分,则需要按照本年度的工分的分红值来慢慢打饥荒。为了好和对方商量,父亲二话不说就把这些票证给了对方。反正自家也没钱去买,放着也是放着,放下没用。
现在大姐和大哥回来了,父亲估摸着四个劳力挣下的工分或许够分粮了,就动起了卖票证的脑子。
其实,这种买卖是很容易做成的。因为城里人有钱又爱穿戴,票证显得很不够用。而乡下人尤其是像我们那样的烂包户子,筛子扣笸篮走风露气不在一忽拦(一忽拦,地方方言,一个地方的意思),谁还能顾下身上的衣服呢?甚当紧做甚哇,自己买是买不起,卖了票证还能打学费,有多好啊!有供有需,就应该有市。
于是,父亲就给队长请了个假,带了所有的布票和棉花票到三岔镇赶集去了。当然他请假绝不能实话实说说自己要去集上卖布票和棉花票,而是找了些别的理由说看病或看亲戚或上事宴什么的。因为他知道票证是不允许买卖的,再说这事传出去也是怪丢人的。他毕竟还很爱面子,因为他是个堂堂正正的“国家六二压干部”。
他来到三岔,发现集市上往年那种繁华的景象不见了,一条大街显得空空落落冷冷清清,只有十来八个骡马拴在围栏的木柱上,还有二十来个人在旁边抽着旱烟说些不相干的事情。他问了一个熟人,才知道市场去年就关闭了——社会主义国家哪里能容得下这种资本主义的交易场所?
父亲在三岔的大街上茫然若失地瞎转达。当他转到了大岳楼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竟然发现有些人偷眉拉眼地在那里做交易,就过去问人家有人要票证吗?几个人围过来稍微讨了一下价钱,就全买走了。刚买走,看到两个戴大沿帽的人从南边的小巷口走了进来,那些做买卖的人说:“快走,快走,鬼子进村了。”如小鸡见了老鹰拔腿就从北面的巷子里跑得无影无踪了。父亲没有跑,他盘算卖下的钱已经装好了,手里什么也不拿的,怕你们做甚?
“你在这里干啥?”一个大沿帽问父亲。
“我啥也不干。”父亲回答。
“你卖布票了吧?”另一个大沿帽又问。
“你怎么知道?”父亲反问。
“你以为我们是吃干饭的?”他们又反问。
“湿的也吃、湿的也吃。可是你们没有看见我卖呀?”父亲一边回答一边提问。
“你说你没卖,那,那几个人(票贩子)跑甚哩?分明是做贼心虚嘛!”
“我哪知道他们跑甚哩。对啊,你说得对极了,他们跑说明他们心虚,我又没跑。”
“你还不老实交待,跟我们走一趟。”大沿帽来火了,知道用这种推理无法对付父亲。
父亲心想走就走,捉贼要赃哩,你见我卖布票了?
父亲跟着那两个大沿帽走进了市管会。没想到一进门,那个大沿帽就让柜台前那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开下一张五块钱的罚款单。他让父亲照单交钱。父亲心想五块钱哩,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娃娃们还等着用钱呢。再说啦,布票是自家的,又不是偷的抢的,自己卖自己的东西,凭什么给你交钱?再说啦,你们又没有逮住我卖布票,给你交钱?我那钱才多哩。给你交了,我便少了,天底下谁不会算这个账。你瞎诈唬,我就掏钱,那我岂不成傻瓜了?正在双方理论中间,从门口突然进来一位被称作是李所长的领导。李所长的出现才使父亲转危为安。李所长看到父亲后马上笑呵呵地上来握住父亲的手说:“哎呀呀,真稀罕哩,我的徐老兄,自从你六二压了以后,咱这还是第一次见面呀。”原来这位李所长当年在公社和父亲同过事,而且相处的还挺好。父亲说:“是哩,是哩,我顾掏坡,一辈子也不进城来,没想到你人家出息了,手下还领着这么多特别能干事情的人。”李所长听着父亲在敲打他的手下,忙让父亲坐在椅子上,又是递烟又是倒水。见父亲和所长是这等关系,那两个大沿帽不好意思地给父亲笑了笑出去了。父亲估计这两个大沿帽定然是出去逮别人去了。罚款的事不了了之,所长还管父亲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
之后,每年布票和棉花票“两票”下来,父亲就跑到三岔赶集去了。而且,市管会的大沿帽再没找过他的任何麻烦。
(未完待续)
来源:《山道弯弯》(作家出版社)

徐茂斌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原忻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忻州市文化局局长。著有《山道弯弯》《徐万族人》《黄河岸边的歌王》(合作)等文学作品。《黄河岸边的歌王》(合作)被收入《中国新世纪写实文学经典》(2000——2014珍藏版)。
热门阅读
“文旅局长带你游山西”系列之忻州篇——来忻州吧 相信你会爱上这座城!
这就是忻州!
游读忻州:“源”来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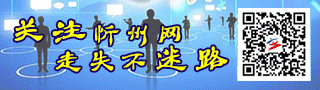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