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会嘉宾合影
2022年6月26日,在“长征解密与文本解码——《乌江引》广州研讨分享活动”中,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斯奋和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等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乌江引》的文体展开热烈讨论。专家们一致认为,这部“伟大长征精神崭新书写”之作具有超出红色题材的重要文学价值。《乌江引》既是长征密电全新解密,也是史诗叙事的文体创新。作为打破纪实与虚构界限的小说力作,这部作品在主题、结构、叙事、人称和语言诸方面的现代性探索弥足称道。这是一部能够真正走向读者的可读性很强的作品,也将是一部具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文学精品。就叙事艺术和美学品质而言,这个文本也是“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这样的文本创新亦可给更多写作者以有益的启示。
作家庞贝的长篇新著《乌江引》今年3月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首印高达5万册。《人民文学》同步刊发,《当代长篇小说》迅即转载。这部作品面世之后迅速荣登“中国好书”、“第一季度影响力图书”等十几个权威月榜或季榜,也迅速登上当当网新书热销榜等榜单。在广大读者中引发热情关注的同时,这部作品在党政军界、史学界和文学界也获得了积极反响。
在本次研讨分享活动中,与会专家从文学原创性方面对这部“长征解密”之作进行了“文本解码”。
史诗:一种现代性
“《乌江引》立体呈现了伟大征程史诗般的庄重和壮阔。”《人民文学》杂志刊发此作时的卷首语中曾有如此表述。长征是一部人类精神的伟大史诗,《乌江引》是向这部伟大史诗的致敬之作,也是这部史诗的“副歌”。作为长篇小说,《乌江引》本身就是一种史诗新文体。在本次研讨活动中,专家们就史诗的概念和史诗性长篇小说形式的现代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红军长征是一部人类史诗,而荷马史诗写的也是古希腊人的远征,这二者应有某种精神气质的相似,一种人类意志力的显示。荷马的《奥德赛》是一种史诗,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是一种史诗,基于这样的认知,《乌江引》作者无疑是找到一种史诗的新形式。假如说《尤利西斯》是一部现代史诗,那么《乌江引》显然也是具有某种现代性,当然,这是与《尤利西斯》不一样的形式。今年适逢《尤利西斯》面世100周年,《尤利西斯》本身就有荷马史诗的原型和母题,因此对于史诗文体现代性的这番探讨更显得饶有新意。

“这样一段革命秘史天然地具有传奇的色彩,往革命历史传奇的路子写本是顺理成章的,庞贝却没有选择这一路径。面对这一题材,他的态度是郑重的。在他眼中,这并非传奇,而是史诗。”青年评论家李德南在论坛发言时说,“通常说到史诗型的写作,很多人会认为,这样作品需要有巨大的叙事体量。仿佛只有如此,才称得上是史诗。然而,在不少作品中,篇幅之长是通过注水的形式来达成的。在这样的语境中,《乌江引》在叙事上的慎重与简约,让我觉得特别可贵。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具有史诗色彩的历史题材,庞贝仅用了十几万字的篇幅予以呈现。这也说明了一点,史诗性作品并非一定得有很长的篇幅。认为史诗型写作必须无限度地拉长篇幅,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专家们认为,长篇小说的现代性,是一种艺术形式上更为讲究的、更为高级的呈现。这种“高级感”,就《乌江引》这部作品而言,就是这种“史诗般的庄重”,一种“更高级的形式感”。“与十七年文学时期的叙事原则不同,今日革命文学写作应是一种现代性写作。与某些新历史主义小说也不同,《乌江引》绝无‘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纠偏。”广州市文学评论家协会主席申霞艳教授说,“史实与虚构之间的博弈,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这种博弈本身就构成一种巨大的张力。庞贝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以自己的小说智慧复活了一个智慧的群体。这使我想到以色列作家赫拉利的那个有名的说法:人类的想象力与信仰有关。《乌江引》这个叙事有一种特别的庄重感,而这也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温情记忆,一种动人心弦的力量,比如作品最后的那几行诗句。对于面对复杂时世的当今读者来说,这是一种很难得的感受。”
文体:一种原创性
长征是新中国每代人都熟悉的历史,但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其实是很鲜见,能说上来的似乎只有当年魏巍先生的《地球上的红飘带》,近年有王树增先生的《长征》,但前者是传统写法,后者是纪实小说,《乌江引》呈现的是一种全新的纯文学写法。与会专家们认为,不必为《乌江引》这部作品贴一个军事题材或战争文学的标签,这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关于这部作品文体的原创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教授曾有如此评价:“这是在文体上的突破,这种革命性和创新性很突出。庞贝打破了虚构和纪实的固定概念,他完全把小说的功能扩大,让我们看到小说的一种新的功能。他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文体。他将读者带回历史现场和语言现场,把历史粗砺的一面以及那个细节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他是站在今人的角度看历史,看革命,看信仰。你一定会被他的叙述所打动。…”对于这种文体创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伍方斐有进一步的阐发:“在解码与编码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乌江引》的时空叙事与主题架构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先锋文学气质。”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丽军认为,《乌江引》是“当代红色革命新琴曲”,其创新性价值在于作者重新阐释历史,建构历史,作品由此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历史主义诗学气质。作者打破单一叙述模式,以新颖的故事结构使虚构与纪实有机融合,在一种虚实相生的变奏中建构现代革命叙述的技术美学。

“《乌江引》具有非凡的语言调性与作品结构,这使得作品能够更加逼近历史真相,并探索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第一部《速写》写长征是一种压抑的、残酷的风格。我在初读的时候会觉得人物不够突出,场面描写过于克制隐忍,主线情节迟迟没有出现。读到第二部《侧影》,我开始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庞贝的抒情描写相当克制,小说语言的调性把握,以及总体风格与隐蔽战场中的无名英雄气质息息相关,丝丝相扣。神秘、诡异、隐忍、克制、密不可宣,悄然而至,静默状态的背后是兵戈铁马,一种反差构成一个巨大的张力。这部作品结构上也是匠心独运,是小结构加大结构。小结构就是《速写》,大结构是《速写》加《侧影》。《速写》中隐忍克制,在《侧影》中得以抒发。”在广东财经大学教授江冰看来,《乌江引》的诗意和抒情也不是我们几十年的常见的传统写法,而是富有质感的大量细节的重返历史现场,强烈的感受扑面而来。譬如过草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乌江引》的描写可谓是再现这个经典场景的“巅峰之作”。
记忆:一个新主题
对于《乌江引》的史学性和文学性价值,北京的专家学者们已有很高评价。就长征题材创作而言,这部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作为红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这部作品也确立了一种文学性新标高。在这次广州研讨分享活动中,来自各大高校的文学教授们也深度阐释《乌江引》的主题意蕴,这是超乎密码情报战之外的另一个很有意味的现代主题:关于记忆与身份。
人们是否有义务记住过去的人和事件?是否存在记忆的伦理?存在的话,人们又该以什么方式来记忆?这是美国哲学家玛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中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历史题材的写作中,几乎无从回避。庞贝《乌江引》的第二部《侧影》是今人的追怀之旅,打捞记忆的碎片,仿佛也是一场梦幻之旅。这个叙事过程蕴含着作者对记忆伦理问题的关切。事实上,“记忆与身份”也是这部复调叙事小说的一个现代主题。
《乌江引》呈现的是人类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情报战孤例,而当年的中革军委二局是一个极为隐秘的存在。那些青春的身影,即使行走在自己的队伍里,他们的身份也不为人知……
“是有这样一个主题,身份与记忆。与记忆有关,也与遗忘有关。当年那些记忆超群的人,他们甚至不能拥有自己的记忆。对于那些普通译电员来说,那些已经破译的密息,他们必须忘掉,‘译过即忘’。因为他们不能掉队,不能被俘。”《乌江引》作者庞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破译三杰’是‘密码脑袋’,他们却不能消除记忆,他们必须记住一切,这是情报分析的需要。因有特别保护,他们一般也不会被俘。万一身陷灭顶之灾,他们唯有选择牺牲。‘三杰’之一的邹毕兆却因用脑过度伤害了记忆力,长征胜利后为失忆、失眠和幻听所折磨,于是向毛泽东请求离开破译岗位带兵上前线。而军委二局创始局长曾希圣终生保守的‘极密’,蒋介石也至死不知此情。曾局长晚年也为这记忆和遗忘(比如张露萍等‘红岩七烈士’的历史污名)而伤神。他们在新中国历史中也有使命和建树,而长征却是他们内心深处最为珍重的记忆……”

《乌江引》作者 庞贝
据悉,此次研讨分享活动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广东省出版集团、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花城出版社、广州购书中心承办,广州市文联、广州图书馆协办。
虚实相生:为了一种新小说
(创作谈)
越过这片亚热带阳光中的烟云,从工作室的窗口向东南方向眺望,不远处就是那个著名历史遗迹的所在。那里有一条“军校路”,有现代化兵工厂,也有一个大门口赫然挂着“外军培训中心”的牌子。冥冥中的缘分,而今我与那座遗址都处在同一座岛上。近百年前的那个秋日,《乌江引》主人公的原型人物,那位叫曾希圣的年轻人,就是一路南下来到这个长洲岛,来到这所黄埔军校。孙中山创办这所军校,蒋介石是校长,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新时代的气息吸引来大批热血青年,他们的校训是“亲爱精诚”,他们的战歌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岂料风云突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曾经的兄弟兵戎相见。及至1934年秋主力红军被迫转移,黄埔四期的曾希圣已是中革军委二局局长了。
这场后来被称作长征的大突围和大转移,共产党的红军是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中寻求一条生路。这个行程是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走夜路”,好在这支“夜行军”是有照明引路的“灯笼”,这便是中革军委二局的破译情报。这是战役情报。二局随时都要回答党中央和军委首长最为关切的问题:敌人在哪里?
回望那段遥远的历史,有时恍若有某种梦幻之感。梦幻中的夜行军,他们一次次绝处逢生,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走向黎明。这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人类意志的胜利。那些“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那些“特殊中的特殊”——军委二局的破译者,长征途中他们几乎破译了敌军所有情报,而敌军对于红军的情报却是一无所获。这是人类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情报战孤例。
关于八十多年前的那场长征,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诸如此类的故事几乎已是尽人皆知,此乃一部宏大史诗的相关章节。《乌江引》所要呈现的是这部宏大史诗的“副歌”,是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传奇。长征密电全新解密,由此为人们解开长征史诗的另一个“密码”。我们歌里所唱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而其神奇的指挥艺术正是基于对破译情报的绝妙使用。这部“副歌”的主角其实只有军委二局的三个人:局长曾希圣、破译科科长曹祥仁、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毛泽东曾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作为小说创作者,有了二局的大量解密文献,如何以文学的形式呈现那样一段秘史,此亦是一个考验想象力的大难题。
《乌江引》是基于准确可考的史实而创作,这个题材给予作者想象和虚构的空间其实是很小。如若做成纪实类的非虚构体裁作品,倒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然而我也眼见坊间某些报告文学作品艺术上的粗陋之相,便决意要将这个题材做成具有文学纯度的小说,一部在叙事形式上具有独特结构、视角、语感和节奏的小说文本,一个独具美学特质的“高级文本”。
所谓“高级文本”,必然要具有很讲究的叙事策略。就叙事文本而言,我们很多作家和读者其实是欠缺某种感知力的。囿于陈规和套路,即便是对于某些传世名著,对其美学品质也往往是无感。譬如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我们似乎很少有人谈论其叙事之美。就叙事技巧而言,这部作品其实是比我们很多纪实类作品讲究得多,这也是我所欣赏的“高级文本”。
斯诺将陕北连绵不断的黄土高坡喻作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令人昏昏欲睡的长句。很多年前的八十年代初,我也曾在军校图书馆里抱着一本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英文原著,昏昏欲睡地啃了很多日子。那时我也有幸读到了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地》英文原著,我至今依然认为赛珍珠也是为我们所低估的一个作家。《大地》写的是我们中国这片大地,而《乌江引》的故事也有“土地革命”这个大背景。母校的那座图书馆,给了我一个世界文学的大视野。小说风格固然可有很多种,但我更爱具有形式感的作品。为独特的内容找到一个独特的形式,甚至是唯一的最佳形式。在我看来,只有内容而形式感欠缺的作品只是半成品,一部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经典作品也理应具有形式的美感。其实也还是“说什么”和“怎么说”这个老问题,但事实上,很多作家仍然只是满足于“说什么”,他们无力解决“怎么说”的问题。
对于小说形式美感的注重,对于这种小说艺术现代性的感知,其实我是从那所军校的图书馆里开始的。2015年深秋,毕业整三十年后,我受邀回母校举办《无尽藏》讲座。听闻学校或将在军改中与其他院校合并,便颇有一番伤感。这所著名的军队外国语学院,八十年代也曾是全国重点大学,那是比当今“985”和“211”之类名份更具含金量。我们外语学院的雏形可追溯至红军时期的无线电训练班,从瑞金到延安,再到新中国,一路跟着走来。那几口接收卫星信号的“大锅”还矗立在大操场边,而长征途中军委二局也是利用无线电信号“从空中找敌人”。曾经的那些辉煌却不为人知的历史,或将随着学校的被兼并而更不为人所知。这样的全国重点大学,却是不挂门牌的,此亦为保密的传统。而这所军校的校址,其实早先也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一个步校。为一个将要消失的传奇而伤感。那些传奇中的人物,他们也到了该被解密的时候了。而我作为创作者,已有了始于这所学校的多年的文学修炼,我有能力以小说的形式呈现这个传奇,有能力在纯粹的史实和虚构的想象之间建构一种新文本。
于是就有了这部《乌江引》。我希望这是一个所谓“高级文本”。就作品形式而言,我甚至也着力为《乌江引》营造一种整体结构上节奏感:《引语》、《速写》、《侧影》、《名录》、《献诗》,整部作品在篇幅构成上有一种特别的节奏感。为此,我严格限定第一部《速写》约占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第二部《侧影》约占四分之一。就叙事视角而言,我严格限定人物活动的“景深”:前景是曾、曹、邹这“破译三杰”,后景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后者只是以前者的视角出现。又如在叙事语言方面,我力求还原当时的语境,而非拘守当今所谓“标准汉语规范”。譬如,在海量的文献阅读中我发现,那时很多人在量词的使用上并非总用“个”字,他们不说“这个土豪”,而是说“这只土豪”。又如,彼时各级指战员他们在口语中并非是喊“政委”,而是“政治委员”。即令是在万万火急的危情时刻,他们也不用这简称。诸如此类的修辞细节,都是构成一个高品质文本的必要元素。我深知即便是处理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题材”,语言也依然应是小说品质的第一元素。
这是一次高难度的创作。党和军队领袖人物的出现,对于作者来说,就不只是要遵从一个“大事不虚”的一般原则,这里所有的细节必须言之有据。我试图以独特的构思解决这个难题,最终文本所呈现的这种“亦文亦史,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正是一种创新性叙事文本的质感。在这个独特的结构形式中,第一部《速写》与第二部《侧影》形成一种独特的复调叙事,这也是某种对位和同构,而《速写》中对“我们”这个给读者以代入感的人称使用,《侧影》为扩展更大历史时空所用的“缠绕式叙事”,亦是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原创性。
《乌江引》固然是长征史诗的一种解密,固然是一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史学界和文学界已有评价说,这是“对伟大长征精神的崭新书写”,而我也要呈现的是人在身心极限状态所迸发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场生命力的“超常实验”,也是人类意志和智慧的胜利。
行走在自己的队伍里,他们的身份不为人知。无尽的时光深处,依然有他们青春的身影。这也是一个关于寻找、关于记忆与身份的故事。即便他们留下的只是一个尘封的侧影,也足可予后来的追寻者以行动的勇气。
点击书封,购买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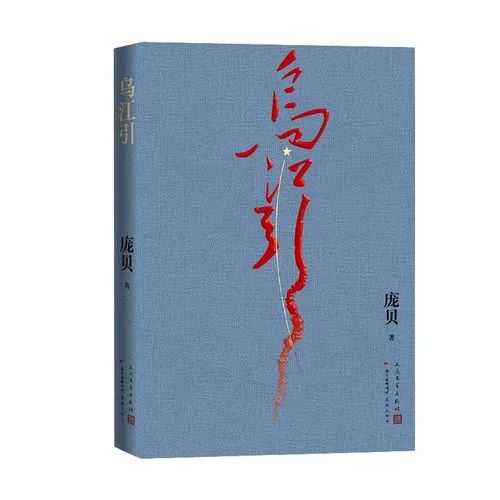
《乌江引》| 庞贝 |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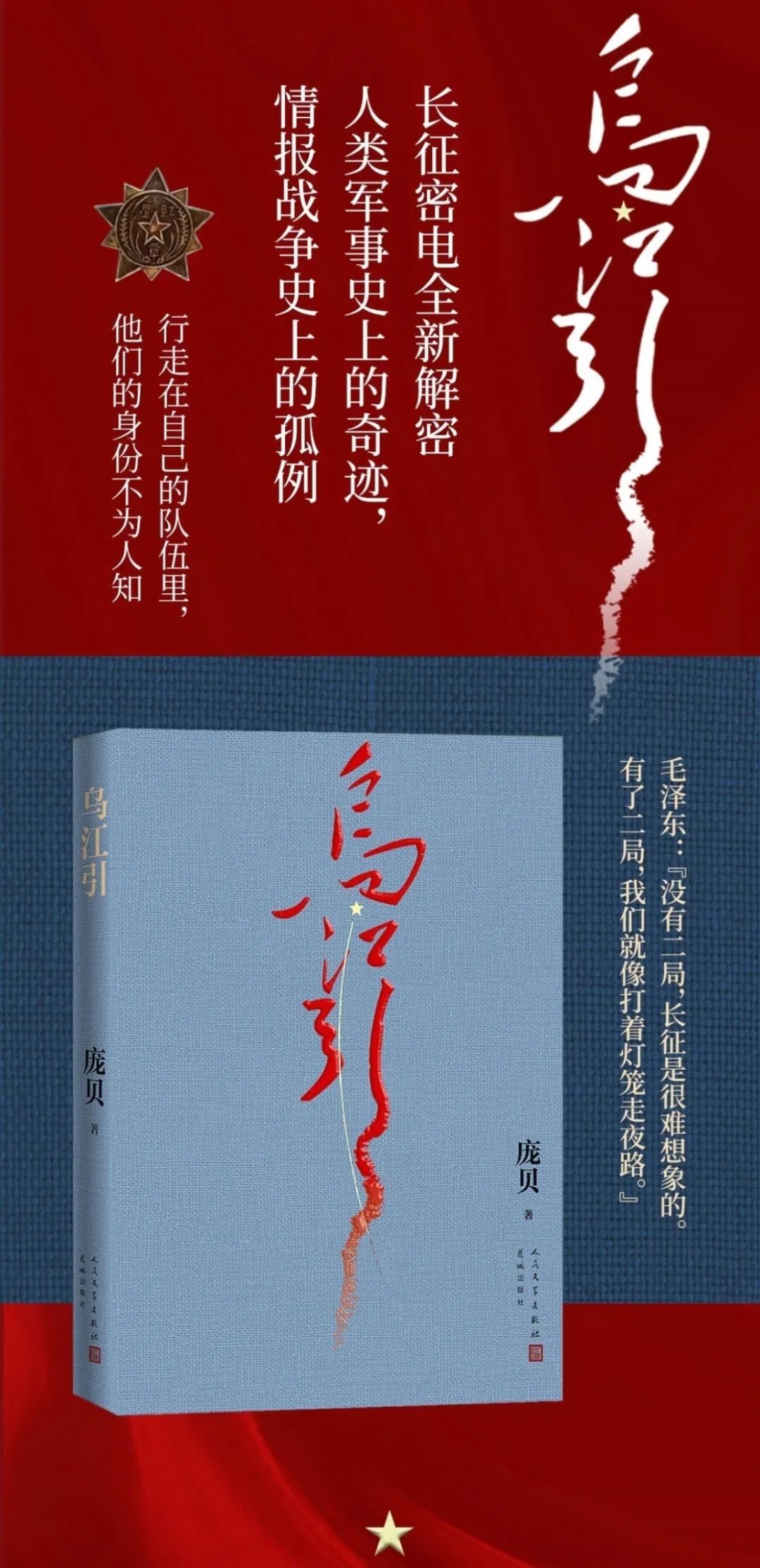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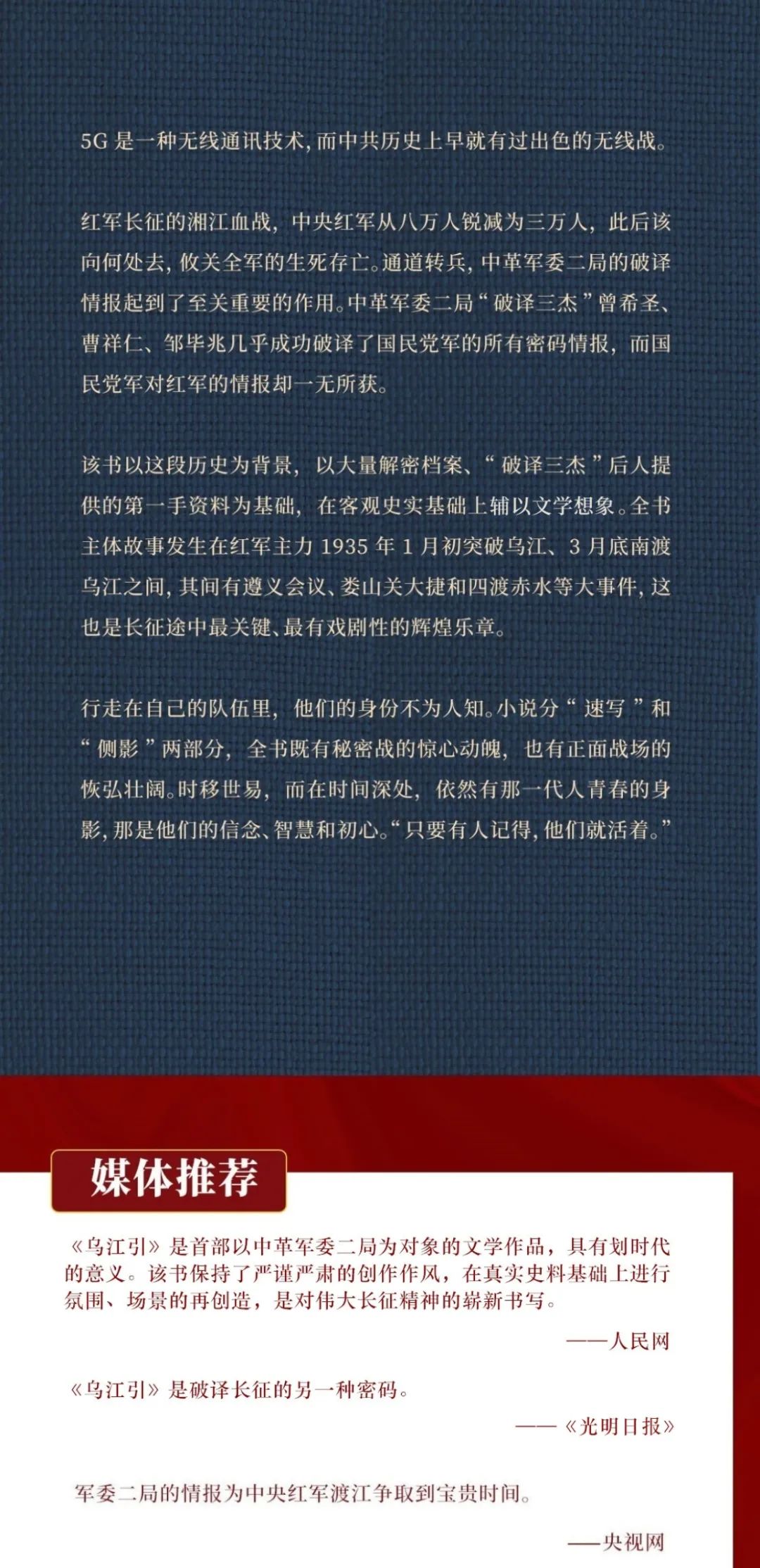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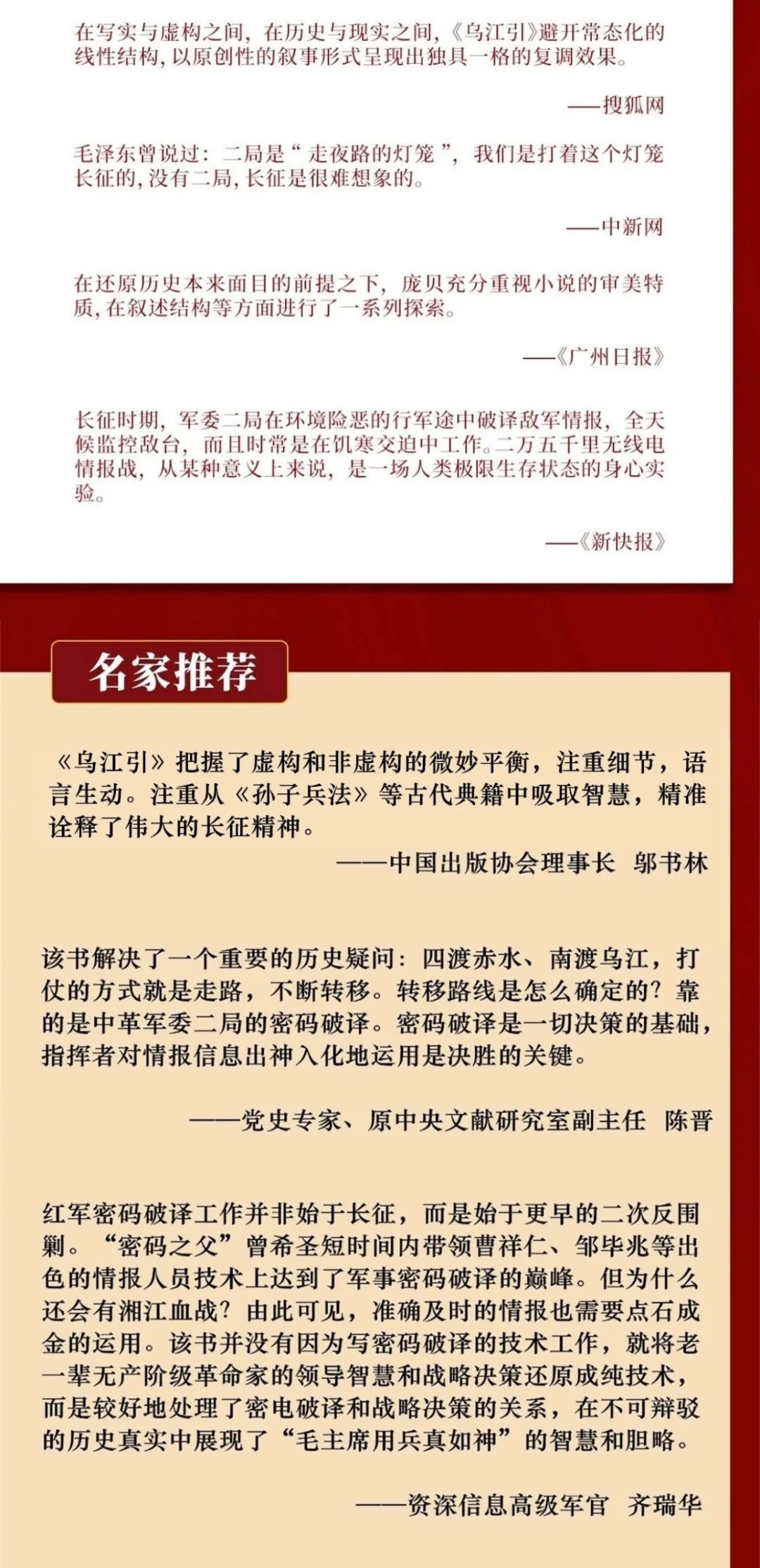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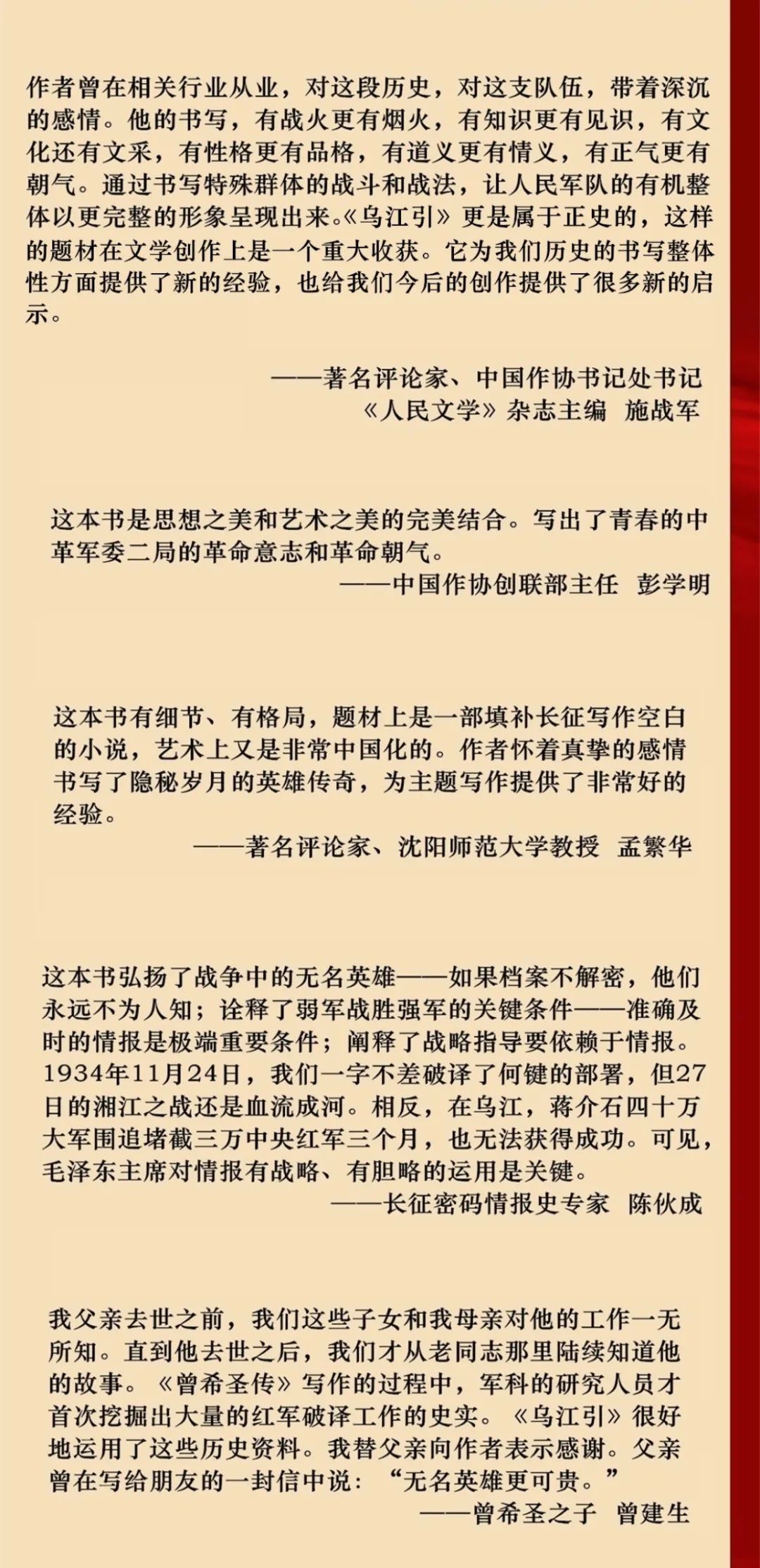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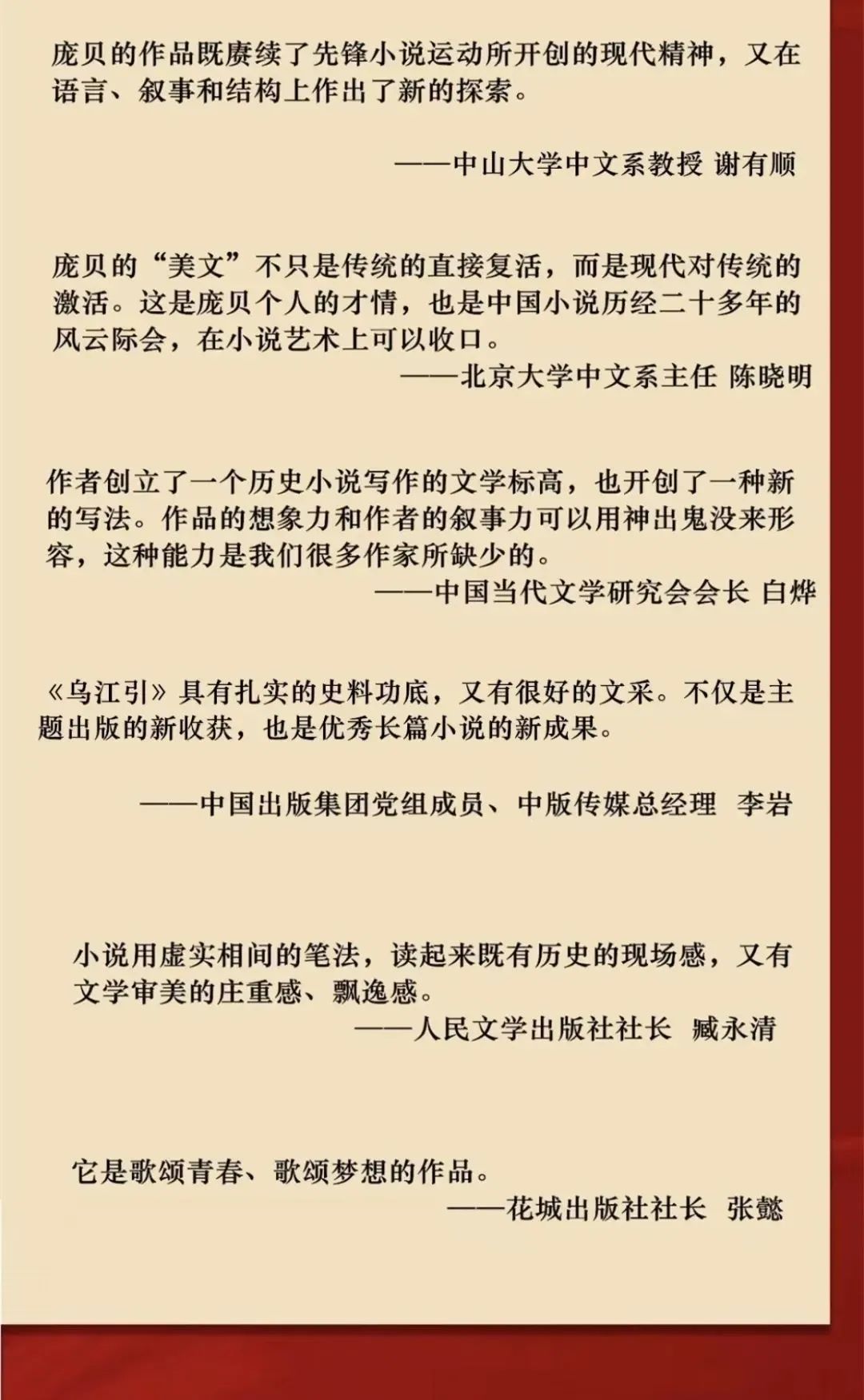

稿件初审:周 贝
稿件复审:付如初、王 薇
稿件终审:王秋玲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