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炜
春节一天天临近。
城里不及乡下年味浓,街道还是车流滚滚,人们仍旧匆匆忙忙。现如今,物质极大丰富,大家吃穿用啥也不缺,缺的是时间和空间,缺的是攒劲过年的那份期盼。
想起多年以前过年的往事,从记忆深处打捞出来,还是那么鲜活,如在昨日,近在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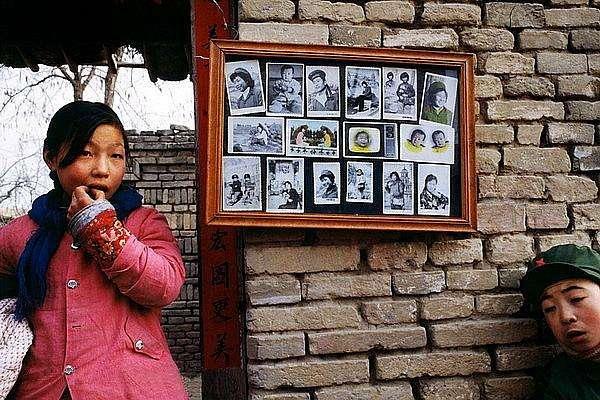
反穿的花棉袄
4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我六七岁的样子,刚上学不久。
该放年假了,镇上的集市一天天热闹起来,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花红柳绿的商品,偶尔还会在某个角落撞见我的一两个看稀罕的同学。
一天午后,我穿过集市早早来到了学校。教室里有三四个同学,正挤着头看一本连环画。我百无聊赖地将几个凳子排成一溜儿,枕着书包要“午休”,却哪里睡得着。刚闭上眼睛,感觉一阵冷风吹过,歪头一看,见一个方头方脑的家伙推门进来了。他叫吴振军,戴一顶雷锋式的“火车头”棉帽,穿着臃肿的蓝花破棉袄,斜挎着一个瘪瘪的书包朝我走过来。我赶紧闭上眼,待那家伙走近时,伸手拦住道:此树是我栽,此道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他没料到桌子后面躺着一个人,着实吓了一跳。他要突破封锁线!我探身一抓,正待合手擒拿,只听“哧啦”一声响,那家伙的花棉袄已经从腋下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我急忙坐起,惊慌失措。
我的眼前是他花白破旧的棉袄,那蓝已经褪成了灰,红的碎花也没了光彩。从那个长长的大口子里,露出土黄色的棉套。
沉默。能听见我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声。吴同学张开胳膊,扭头看看他左臂后面那片耷拉下来的破蓝布,又回头看着我。我心想这下事闹大了,要赔人家的棉袄!回家还少不了挨顿打。

突然间,吴同学仰头哈哈大笑起来,像是捡了个大便宜。他对我说:不碍事儿!这是俺妈做的新棉袄,面儿是新的,里儿是俺姐的旧布衫改的。正不想穿它了!说着,他翻开了棉袄的衣襟,一件质地细密的崭新蓝士林棉袄露了峥嵘。
虽是严冬,我的手心还是出了汗。好险啊!
第二天散学典礼,我旁边的吴同学已经提前十天穿上了他要过年才能翻过来的新棉袄。
我不敢肯定,现在已是老吴的振军同学是否已忘了他当年的那件花棉袄,反正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的那件新棉袄的旧里子,竟然跟闻名世界的“功夫熊猫”破裤头上那块补丁的图案一模一样!30多年后,当我在银幕上看到熊猫屁股上的那块蓝花布的时候,我一下子喊出了一个名字:吴振军。这真是太神奇了。吴同学那富有创造性的“一虾两吃”的穿法,化腐朽为神奇,变戏法般地将那个少皮没毛的破棉袄一下子变成了蓝格莹莹的新棉衣!
三个红衣大炮
“腊八祭灶,年下来到。小妮儿要花,小小儿(男孩)要炮,老婆儿要衣裳,老头儿打饥荒……”这是我当年的小伙伴们经常在春节来临时唱说的顺口溜。几十年过去,这样的童谣再也没人提起。但它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那一年,我回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年。
已是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我跟着我的爷爷去离家三里远的龙王庙村赶年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豫东农村的年集,既有古老的传统民俗,又有浓郁的时代氛围,赶集置办年货的人摩肩接踵,扎摊卖东西的人吆喝不绝,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手里提着年货,脸上挂着喜庆。鲜艳新潮的革命样板戏宣传画和古朴深沉的木版水印年画肩并肩摆着,广口玻璃瓶里晶莹剔透的球形水果糖和案板上粘满芝麻的长条麻糖相安无事,炸声脆响的新式电光快鞭和雷声滚滚的乡村土炮仗相互叫板难分高下……真是琳琅满目,各有千秋!

那天,我爷爷领着我在一家卖大雷炮的摊上买了三支“红衣大炮”。再看那大炮仗,烧火棍般粗细,半截铅笔长短,朱红的炮衣光灿灿美艳艳夺人眼目,蜡黄的绵纸一层层一圈圈致密无比,其头顶有圆弧帽儿、屁股有金封泥,不长不短不粗不细饱噙火药的一根铅灰色炮捻儿支楞楞齐崭崭,一副威仪堂堂貌,绝对炮中伟丈夫。近前闻闻,一股火药的异香瞬间降服了我,竟使我有些晕眩。
那天上午,我爷爷究竟还买了些什么年货我忘了,那三支红衣大炮花了多少钱我也记不真切了,反正也就是几毛钱。在那贫寒的岁月,钱对于靠种地挣工分的我爷爷来说,一厘一毫也不敢浪费。我捧着那三“尊”红衣大炮,也捧着新年和希冀,跟随我的爷爷回家了。
携着铺天盖地的一场大雪,春节终于来了!
大年初一大清早,在“噼噼啪啪”响成一片的鞭炮声中,我们的红衣大炮登场了。爷爷一手拿一根燃着的麻秸,一手接过我递给他的大红炮,用两个手指夹了,沉着而坚定地点燃了炮捻,如同点燃了新的希望。在急速的“哧哧”声中,他老人家将希望高高抛向空中。
红衣大炮在头顶炸响!
“嗵”——声沉如雷,直冲霄汉。周遭鞭炮顿时喑哑,直“榨”出它们“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嗵”——地动山摇,鸟飞兽走。使胆小之人“两股战战,几欲先走”;
“嗵”——电光闪过,天宇走红。一片片鲜艳炮衣在鹅毛雪的簇拥下纷纷飘落,像三月雨后的桃花瓣。一时间,“六宫粉黛无颜色”!
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我的爷爷仰天道:吉兆啊!
就在那天,我的爷爷告诉我,正是在撒满红色炮衣的那个地方,曾经落下过国民党军队的一颗炸弹。
那是1948年的夏天,睢杞战役在我的家乡打响。当时,我家的院子是粟裕将军麾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指挥部。战斗异常激烈,国民党军的飞机疯狂俯冲投弹。其中一颗,呼啸着自天而降,斜刺里飞向我家。刹那间,那个半人多高、三把多粗、黑不溜秋的铁家伙穿过老榆树的树冠,深深地杵进了地面。
幸运的是,那棵炸弹没有炸响!新中国成立后,那个哑弹被村人锯开,顶端的一截儿,挂在村口的老树上,成了生产队上工敲的钟。我小时候曾经听过它发出的声音,悦耳且有穿透力,绝对非同凡响!
往事如烟。
几十年过去,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姓每天都像过年,生活富足、多彩、幸福。而那些我们曾经走过的年,还有那些有关过年的故事,就留在了我的脑海深处。
等老的时候,佐酒。
编辑:王向前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