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档案】蒋孔阳(1923-1999),著名美学家,四川万县人。1941-1946年就读于中央政治大学经济系。1948年进入上海海光图书馆从事文学方面的编译工作。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副会长、上海美学学会会长、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有《德国古典美学》《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美学新论》《文艺与人生》等,主编《哲学大辞典·美学卷》《辞海·美学分册》等,论著辑为《蒋孔阳全集》。1991年获“上海市首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爱上美学,一颗彷徨不安、不断探索和追求的心总算有了着落
“如果我也谈得上受到过什么美的熏陶的话,那么就是我家乡的那些山,以及山间的泉水、树木和白云。”1923年,出生于四川省一个群山环绕的闭塞村庄,幼年的蒋孔阳自然与一切文艺作品绝缘,看不到任何戏曲、电影、话剧和舞蹈。但他年轻时就喜欢跋山涉水,常常“如醉如狂”般地看着漫天的红霞,对着小溪痴痴的发呆。正是这些幼年时对自然美的直观感受,引领他走上美学之路,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一生的美学追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量新文化新文学的著作涌进万县街头,中学时期的蒋孔阳第一次看到了鲁迅、郭沫若、冰心等人的作品,也第一次看到了《大众哲学》、《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一类的书籍,“它们像闪电一样打开了我的心扉,使我热爱起文学和社会科学来”,这让自觉年少时“浑浑噩噩”的他一下子看到了人生的方向,在高中便决定致力于学术事业。
但命运却给蒋孔阳开了一个玩笑。1941年,本来想考西南联大的蒋孔阳因病错过了考试,只能去考尚在招生的中央政治大学经济系。虽然学校附近有“旖旎的花溪,奔腾的虎啸口”这样的美景让他整日徜徉,可他对经济系的课却怎么也提不起兴趣。他一有空就扎进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喜爱的文史哲著作。其中,他尤为钟爱那些“富有哲理性的文艺作品”,以及那些“富有文艺性的哲学著作”:无论是冯友兰的《新理学》、宗白华的《流云小诗》《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方东美的《科学哲学与人生》以及屈原、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滋养他精神家园的食粮。
在大学期间,他就曾写信向宗白华教授请教学问。宗白华先生后来回忆道1942年曾收到“一位中学教员的来信(蒋孔阳曾因母生病休学一年,在中学任教)并附有一篇论文,这位教员和我素不相识,但他的论文写得很有水平,我便把这篇论文刊在《学灯》上……这位当时不知名的中学教员,就是上海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
1946年,蒋孔阳从经济系毕业后被分配进入一家银行工作。这份一年能拿18个月工资的工作,是当时人们梦寐以求的“金饭碗”。但他反而自嘲自己整天是坐以待“币”,乏味难耐。他于是常常请假去南京中央大学里蹭课,内心依旧放不下校园生活。一日,他在夫子庙的旧书店闲逛,突然瞥见书架上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那书名就像磁铁一样让他再也挪不开脚步,“从此,我知道天地之间还有一种学问叫‘美学’,而我自己就朦朦胧胧地爱上‘美学’。”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48年。当时,著名学者林同济先生邀请他来到上海海光图书馆担任文学方面的编译。欣喜若狂的他,即便使出“装病”这种理由,也要尽快从银行辞职。至此,“一颗彷徨不安、不断探索和追求的心,总算初步有了着落。”此后,他向着美和真理不断探索、不断耕耘,一直到自己生命的终点。

年轻时的蒋孔阳与夫人濮之珍。“生命是只永不颓蚀的琴弦,待我俩去奏出谐和而永恒的乐曲。”60多年前,他们一同进入复旦中文系,一个教《文学引论》,一个教《语言学引论》,被朱东润先生戏称为“双引楼”。他们在教学相长中成长,一位是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一位荣膺上海市第一届语言学研究“终身成就奖”。他们的爱情故事成为复旦的佳话,学校曾授予二人“比翼双飞”奖。
像屈原一样工作,不马虎;像陶渊明一样生活,不计较
1951年,蒋孔阳应聘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担任文艺理论方面的教学工作。来到了更宽广的学术舞台,年轻的他自然想有所作为,也很快就在学界崭露头角:1953年,《要善于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英雄人物》发表,成为他“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起点”。与此同时,他开设了《文学引论》等课,并且教学相长,将讲义编成《文学的基本知识》和《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两本书,都引起了广泛反响。仅仅《文学的基本知识》一书,在1957年出版后的几个月内,就卖了20多万册。但“缺乏政治敏感”的蒋孔阳没有意识到,这些著作在日后留下了隐患。
1960年,一个普通的早晨,没有任何预兆,对蒋孔阳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开始了。期间,他不能上课,不能参加相关活动,走在平时熙熙攘攘的复旦校园,“像走在沙漠里一样”。终日无所事事的他还买了月票,从一辆公交车的起点坐到终点,再坐回来。就像在城市中找不到目的地一样,他深感到,“一个人生活在社会,最可怕的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找不到贡献自己力量的地方。”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打击,蒋孔阳最终依旧是依靠对学术的热爱走了出来,他自己回忆这段经历时反而风轻云淡,用他的话说就是“从震惊到木然,从木然转而释然了”。
他曾在一本书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不能因为知道自己有一天要死,因此就不生活。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诚实的工作有一天会遭到否认,因此就不诚实地工作。诚实地为人类的幸福去工作,是自己的使命,至于困难和打击,那就让上帝去安排吧!”这种“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的乐观与豁达,成为蒋孔阳一生的信条。晚年,在《只要有路,我还将走下去》一文中,他祈望人应当“像屈原那样工作,不马虎;像陶渊明那样生活,不计较。”
1961年,蒋孔阳重新开课,改教西方美学和美学,这对他来说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园地”--早在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他就曾发表《简论美》《论美是一种社会现象》等美学论文,在当时很有影响力。1964年,结合教学,他开始撰写《德国古典美学》一书,完成初稿。同年,着手翻译《近代美学史评述》,并于次年译竣。但不久后,“文革”开始了,这些工作都陷入停滞。尽管学术工作停摆,但他还是利用可能的时间潜心学问,一本重要的著作《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1986)就是他在文革后期“靠边”“靠”出来的:1975年,他从崇明干校回到复旦,但还不能教书,成了“闲散”分子。利用这个机会,他天天跑到图书馆,阅读各种有关先秦音乐美学的古籍资料,逐步搜集整理起来,就有了该书的初稿。这种坚持,也最终换来了文革结束后的“厚积薄发”。仅在1980年一年间,包括《德国古典美学》《近代美学史评述》《形象与典型》《美和美的创造》《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在内的五本书同时问世。许多人盛赞他的神速,他却说,“他们哪里知道,这‘神速’是多少年的汗水和泪水、经过多少年的积压,而后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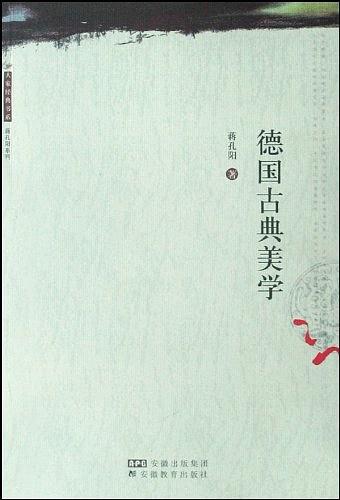
《德国古典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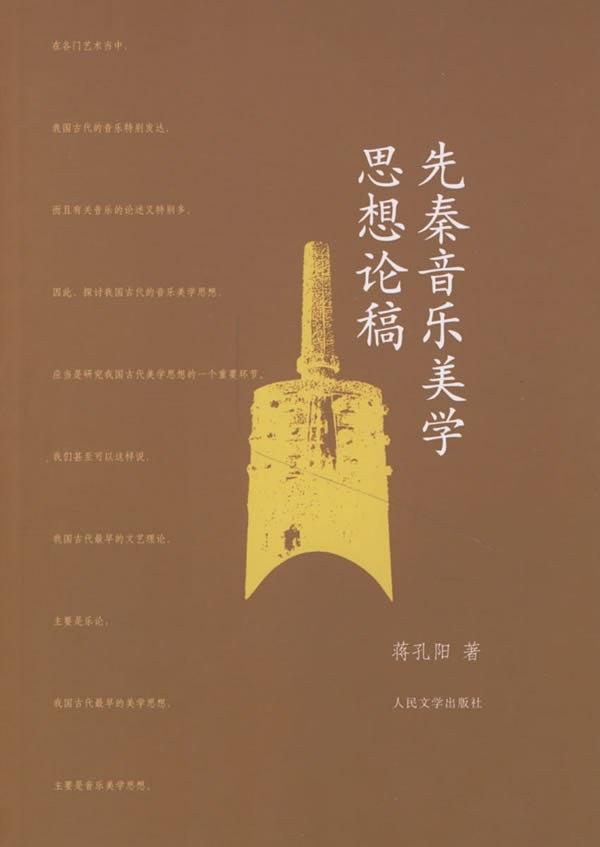
《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
80年代,蒋孔阳迎来了学术人生的“最佳时期”。作为“美学热”的参与者和重要推动者,他的《德国古典美学》和《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一经问世,就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认为是中西方美学断代史的拓荒之作。其中,《德国古典美学》更是被誉为“美学热”中“美学知识传播的经典论著”。但他的研究并不止步于美学史,而是进一步向“科学的高峰”攀登,开始从理论高度总结和反思美学的原理问题。1983年,他正式开始撰写《美学新论》这部耗时长达10年,凝结了他毕生美学思考的著作。这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当代美学中一个新的派别--创造论美学的确立。
但学术的精进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流逝。晚年,蒋孔阳身患帕金森病,行动变得不便。但他却依然怀着一颗“把生活燃烧起来的心”,用积极的人生态度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最后十年,蒋孔阳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美学新论》和《文艺与人生》、自选集《美在创造中》和《美的规律》,主编了《哲学大辞典·美学卷》、《西方美学通史》等大型学术工程。而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心念念的还是美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还想着出院后,再将《文集》的稿子看一遍……
他的美学思想自成体系,是一种通向未来、生机勃勃的美学
美是什么?从古至今所有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反复追问,建构起了千年来的美学思想史。而这,也是蒋孔阳终其一生孜孜不倦的求索。在1993年出版的那本《美学新论》中,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美在创造中。”
“看似普通的一句话,却是当代美学一个巨大的推进和突破。”蒋孔阳的学生、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朱立元这样说,“在传统美学史中,美学家们往往试图为‘美’找到一个最恰当最完美的定义。可是美太丰富、太复杂了,任何定义都不过是一得之见。而蒋先生突破了研究‘美是什么’的本质主义思路,开始思考‘美是如何生成的’这样一个事实上关乎‘美的存在’的问题。这是对近代西方认识论美学的重大扬弃。”
因此,在蒋孔阳那里,美不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是人们在具体生活实践、在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恒新恒异的创造”。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美是多层累的突创”。他曾以星空为例来说明:群星璀璨的星空自然是美的,但这种美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当然,首先要客观因素的存在,有星球群、有太阳光以及黑夜的环境;其次还要有文化历史所积累下的各种关于星空的神话和传说,这些星球的美才富有更多意蕴;最关键的还有观赏星空的人,他们各自所具备的心理素质、个性特征和文化修养,会使他们在观赏同一片星空时,品味出不同的韵味和美。“这样,星空的美,是由多种因素、层层积累,到了条件都具备的时候,然后突然创造出来的。好像发电的设备都具备了,然后电钮一揿,电灯便亮了一样”。
这一“以创造论为中心的美学思想,像一根红线鲜明地贯穿在他的美的规律论、美感论、审美范畴论等等全部体系中”(童庆炳语),构成了他独树一帜、恢弘气派的思想体系,即“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学说”。
“以今天的眼光审视20世纪中国当代美学史,有些学者曾诟病,把美学认识论化,是中国当代各派美学难以取得新的进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把蒋孔阳先生的美学思想也囊括其中,我认为是有失公允的。他的美学思想已经突破了单纯认识论哲学的窠臼,是一种通向未来的、生机勃勃的美学,对我们今天建设、发展美学学科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朱立元这样说。

《美学新论》
在蒋孔阳的理论大厦里,美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恒新恒异的创造”。对待学问,他也始终秉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谈及撰写《美学新论》的感想,他曾说:“人生在不断前进,不断创造,学术更应当不断前进,不断创造。在这前进和创造中,我们固然要道通为一,‘一’以贯之;但我们千万不能固执于‘一’,蔽于‘一’,以致陷在‘一’的死胡同里。我们要条条道路,广通天下!”在他看来,真理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他特别服膺马克思的一句话:“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因为并不认为自己占有真理,他总是感到自己的不足,总是虚怀若谷地张开双臂,去听取和吸收别人的意见。
在50年代“美学大讨论”时期,有人问蒋孔阳是哪一派?是朱光潜派?或是其他派?蒋孔阳明确地回答:“我从每一派那里,都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但它究竟属于哪一派,我却说不清楚。就好像呼吸空气,我很少注意哪些是氧气,哪些是二氧化碳,我只是呼吸罢了。它们营养了我的身体,我就感到满足了。”
正是这种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学术品格,成就了他“综合百家之所长”、兼收并蓄的理论体系。从理论来源看,蒋孔阳的《美学新论》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基础,综合吸收了他之前的研究对象包括先秦诸子、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朱光潜、宗白华等人在内的美学思想,在中西对话、古今转换的宏大视野下,将中、西、马美学思想融会贯通,逐渐建构起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这是一种不设框框,善于吸取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因而具有生命力的美学”(钱中文语)。这种美学研究中的对话思维方式,也为21世纪美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正因为这样,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曾评价《美学新论》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总结形态”。
像庭前的阳光和绿草,多作奉献,把生命和美奉献给人间
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已公认,蒋孔阳的美学思想自成流派,但他自己却始终秉承着一种“理智的谦逊”,素来不以什么“名家”或“大师”自居,更不标榜自己是美学领地里的真理桂冠占有者。蒋孔阳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郑元者说:“蒋先生很反感被归入任何派系,对做学问所存在的‘派系’问题也予以过批判。他始终认为学问应以真理为线,而不是以派性和门户为线。当别人把他作为研究对象时,他总会随后就说‘研究的对象太普通’之类的话。”
朱立元也回忆起这样一件往事。在《德国古典哲学》刚出版之际,他曾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评论,在称赞《德国古典哲学》的同时也提出了四点批评。当时在日本访学的蒋孔阳看到后立刻回信,称赞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值得学习”,而对他的批评还“太客气”,自己“有机会一定加以修改”。“蒋先生对学术的这种热忱和谦逊让我终身难忘。”他这样说。

对朱光潜、宗白华这样的美学前辈,他充满尊敬;对年轻后辈,他也是平等待人、关爱有加
为学是这样,为人上更是如此。为了美学的发展他尽其所能,特别是对后生关爱有加,放下自己的工作也要为他人“做嫁衣”。晚年,许多素不相识的年轻后辈著书后向他索序,他从来都是有求必应。“都是搞美学或文艺理论的,答应了这个,推辞了另外一个,不好,于是我办得到的,我都尽可能答应”,他就这样陆陆续续写了100多篇序。为了写序,他要读动辄几十万字的原稿,这耗费了他大量做学问的时间和精力。许多学者都说,若不是为太多人写序,蒋先生的《美学新论》早在80年代就应该完稿。家人也因此戏称他是“门诊医生”,“不看主要病人,专看门诊”。但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事情,蒋孔阳还是坚持要做,因为他觉得“目前的学术界不是著作太多,不是水平太高,那么相濡以沫,相互鼓鼓气,这对于繁荣我国的学术,不是非常必要的吗?”
这种真诚和奉献的精神,贯穿了蒋孔阳对学术、对真理、对美的追求之中。他学术之进取和为人之宽厚,相互之间早难以分离。文艺理论家钱中文曾这样总结蒋先生的学术和人生:“蒋先生与现今的不少美学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把美学理论的求新,与他作为人的自身的完美追求,水乳交融地结合了起来。这意味着他把自身的生命意趣,投入了人生价值的追求,在美的理论的提升中,也增进了探求者自身作为人的觉醒,自身人格的升华,从而成为我们时代的真正的智者。”
契诃夫曾经说,人越靠近真理,他就越单纯,越容易理解。蒋孔阳的一生,不仅是探寻美、探寻真理的一生,也“知行合一”地诠释了什么是人格美、什么是美的人生。正如蒋先生在《且说说我自己》一文中对自己的总结:
“我是一个书生,百无一用。我唯一的用处是读书。读书的目的,是要增长知识,明辨是非,活跃思想,探寻真理,提高人的价值。但人的价值,不在于战胜他人,夺取个人的桂冠,建立自己的体系,而在于把自己提高到宇宙社会中来看,让人认识到天地之大,人生之广阔,真理不是一个人独占或包办得了的。我们应当像庭前的阳光和绿草一样,多作奉献,把生命和美奉献给人间。”

作者:陈瑜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杨逸淇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